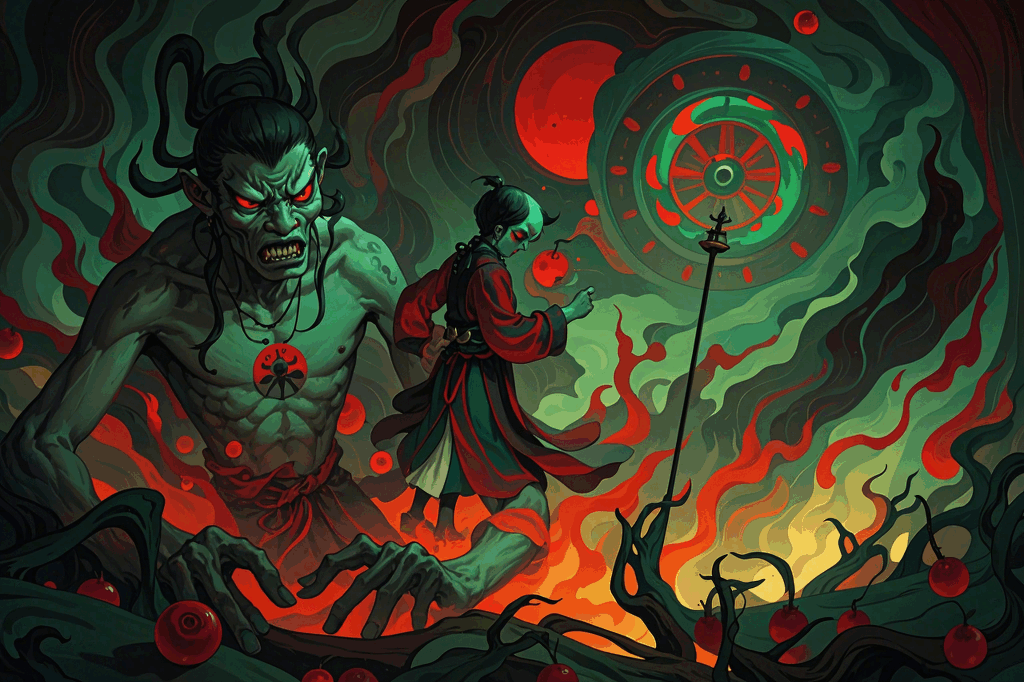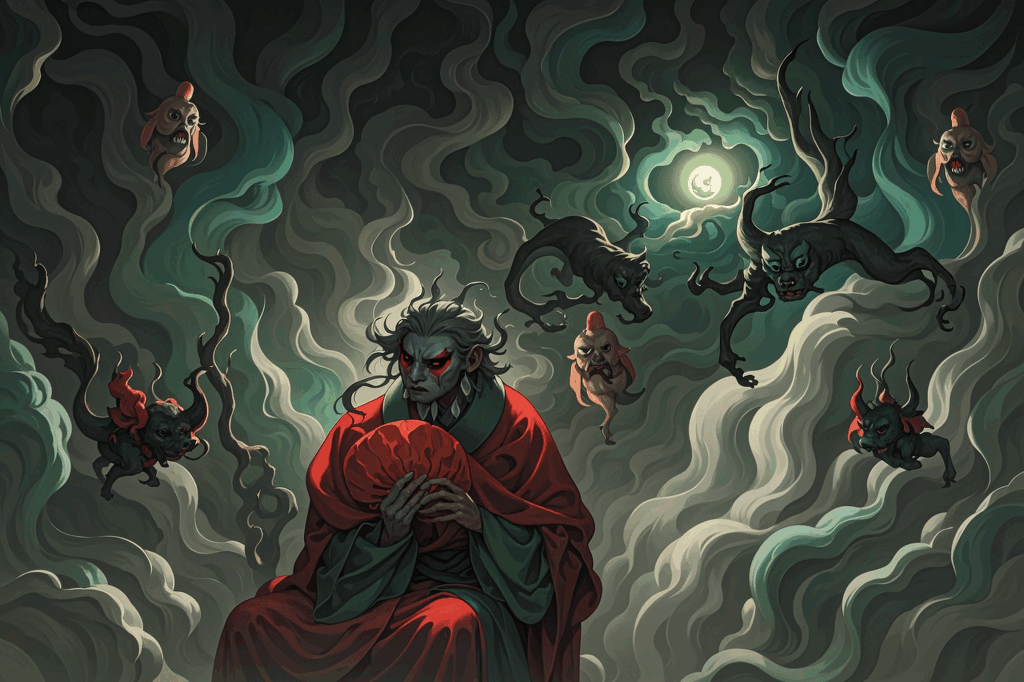13
这个故事要从哪里讲起呢?
所谓的真相。
那什么苏显宗虽然不是东西,但他还是有一件事看准了:我的确是个骗子。
职业骗子。
最初我搞诈骗,卖假的保健品,但效果都很一般,没挣到几个钱。
后来,我发现女人更好骗。
太喜欢听甜言蜜语,太容易被感动。
于是我仗着自己长得好,身体好,经常以谈恋爱为名,骗女人。
就、拐卖。
拐到西部山区的,给光棍做老婆,拐到东部富裕地区的,强迫坐台,还挣得更多。
我为什么要做这种生意?
不知道。
这事我从记事起就一直在做。
我 8 岁逃离我妈出来流浪,拜当年那个给我送饭的小姐姐所赐,捡回了一条命后,就在社会上东混西混,后来跟了位大哥。大哥看我嘴甜会哄人开心,说我天赋异禀,就带我当骗子,挺多年了,一直干着。
苏米只是我其中一个目标。
不过说句实在的,这女的还真单纯啊,我是她第一个男人,她还真爱上我了,爱得要死要活,连我都觉得夸张。
我什么都没有,她还一心想嫁给我。
成天问我什么时候结婚。
我嫌烦,就找了个办假证的,鼓捣了张假的结婚证安她的心。
她居然信了,奉若珍宝,淘宝了纪念册裱起来。
我看着都想笑。
苏米是我遇到的,最好骗的女人。
她就跟个祥林嫂一样,絮絮叨叨跟我说了很多她爸爸的事。
一看就缺爱。
我投其所好,关心、安慰她。
实话说这种女人最好骗了,苦惯了的人,给那么一丁点甜头,就足以让她死心塌地。
她还真死心塌地了。
特别是搞到假结婚证后,她就真将自己当我老婆了。
洗衣做饭,畅想未来,还靠着我的肩膀,跟我说她想给我生孩子,最好是一儿一女。
我就比较无奈了。
我其实没有爱人的能力,不是我不想而是我没有爱人的能力,我个人感情比较平淡稀疏。
不只是针对女人,我对谁都是。
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原因,还有我幼年流浪的经历。
导致我成为了这种人。
但没办法,我就是这种人。
我喜欢钱,喜欢骗钱、花钱、浪,对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看得非常淡。
我是亲生的,我妈为了钱,为了过好日子,尚且要把我给阉了,这世上还有什么可以相信?
苏米长得比较好看。我将她卖了五万八,平心而论,这个价钱已经很不错了。
我挥霍了一阵子。
爽。
突然有一天我路过一个电话亭,看见一本悬疑小说。
我也是手贱,阴差阳错就把那小说给拿起来了,看了一会儿,觉着写得不错,一环扣一环,还洋溢着诡异的死亡气息,蛮精彩的。
随意看了看封皮上的作者名,竟然是苏米。
我心里头一颤。
怎么,这女的是,阴魂不散?
我一定是遇到个同名的了。
结果再翻一页,我看见书里头有那作者照片,竟然真的是我卖了五万八的那个苏米。
天呐!
我这可太亏了。
没想到那苏米是个有钱人。
看不出来啊。
我粗粗估了一下书的销量,按普通的版税算,一年也有上百万。
但她的消费水平我记得是一般啊,我哄她还贴了点钱呢。
难道,是深藏不露?
好家伙。
我找到了发财的渠道。
可是,我已经把这家伙卖了,卖了五万八。
我简直是买椟还珠啊。
我的笑容凝滞在了嘴角,手里头的可爱多也融化了。
我、我这还能补救吗?
哦,我想起来了。
我卖她的时候,是用迷药将她迷晕了的,她没有看见我的脸,她什么都不知道。
成了!
我一拍脑门儿。
我想到办法了。
我找到中间人,打听了下她被卖到哪里了,然后披星戴月赶往那个小山村。
那一刻,我就像个从天而降的英雄。
降落在她最落魄、最无助的时候。
不是我说,苏米这人骨子里是有那么一丝倔的,大概是因为读了点书的缘故,她死活就是不认命。我找到她的时候,她被用铁链锁在猪圈里,肚子也已经大了。
但还是犟着不跟人家过日子。
我都不知道她在犟什么。
我调整了下情绪,抱住她失声痛哭。
然后特别虚伪地说谢天谢地,我可算把你给找回来了,亲爱的,我想死你了。
她有些呆滞,空洞的眼神死气沉沉。
过了大概有二十分钟吧,她整个人才有了那么一丝生气,看着我的眼神开始躲闪,我抱住她,她闭上眼,哽咽着跟我说对不起。她尽可能地弯下腰,用身上被扯得稀碎的破布,去遮挡她稍稍隆起的小腹。
我知道她在说什么。
我有点无奈,有点哑然失笑,还有些说不出来的感觉,很久后我才明白,那种难以名状的感受,叫心酸。
但我当时觉得也就这样。
我当时满脑子都是:卧槽!这家伙是个富婆,赶快想办法把她骗个倾家荡产。
我怀着各种各样的小心思,将苏米带回家去(当然伪装得曲曲折折,好像是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把她给救出去)。我甜言蜜语哄着,好吃好喝供着,挖空了心思抚慰着。
我想了个妙招。
我娶了她,那就能占她一半财产。
她是独生女,她爸的拆迁款,以后都是我的。
可是我的结婚证是个假证,想想真懊恼,我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但是我不会气馁,大不了将结婚证弄成真的就是。
于是,我找了同行会仿妆的那个“女医生”,然后拿了苏米的身份证,让她伪装成苏米,我俩将结婚这事坐实了。
哈,我真是个小天才。
等到我的甜言蜜语,让苏米的情绪稳定后,我开始旁敲侧击:“怎么,老婆,你是个悬疑作家啊?我看过你的书,写真不错,你卖出了这么多本,版税收入应该有一点吧?”
苏米的眼眸黯了半分,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钱都在她爸手里,说是给她攒起来,以后当嫁妆。
呵。
嫁妆?
那岂不都是我的?
但我记得苏显宗一直不待见我,总说我是骗子,还请过人调查我,死活不让我跟苏米结婚。
我知道后很不开心。
他要连钱都攥走了,那我还混个屁啊。
我叫苏米问苏显宗要过一次,当然是没要到。
我就自己去找苏显宗了,把红彤彤的结婚证甩在他眼前(这时候我底气足了),我说苏米都这么大了,我都跟她结婚了,你还握住钱,这算个什么事嘛!不厚道了吧?
苏显宗应该是被结婚证刺激到了,歇斯底里起来,还跟我打了一架,当然没得打过我,反倒把他自己气得吐血。
他指着我的鼻子说我这个骗子,他就算把钱烧了都不给我。
我虽然生气,但这倒没什么关系。
老匹夫,等他死了,什么都是我的。
但这苏显宗不知道怎么回事,还真是跟我铆上了,他跟个间谍一样,雇了人去查我的老底,还真给他查出来了。
他要是暗搓搓报警,那我还没辙,可能就真栽了。
但他偏偏给我来了个电话,威胁我说,我所有的事情他都已经知道了,叫我赶快离开他女儿,好自为之。
果然是文人出身。
没见过我们这些地痞流氓。
威胁?
威胁有用?
听说这段时间,他跟那个寡妇情投意合,两个人想结婚了。
那他的拆迁款,岂不是还得分给寡妇?
那我玩个屁。
但凡我出手,断没有空手而归的道理。
威胁?
谁怕谁啊?
我一不做二不休,跑去见了苏显宗一趟,丫的跟我跳脚,让我滚出他女儿视线,还要拿脚踹我,我想都没想,一把将这老不死的给推下楼,直接摔成肉酱了。
反了他的。
是的,我故意的。
接下来就是我的表演了。
这时候,就要隆重请出,我的好搭档,仿妆高手,“女医生”了。
本来她就跟苏米长得有点像,这再借助她强大的仿妆技术,就几乎能以假乱真了。
我们玩了一手“精神分裂”“人格分裂”,还让警员左诀做见证,加上苏米这家伙本来就是有点心理疾病的,她文风暗黑,是众所周知的事。
我们玩了一套精神分裂的小把戏,让警方相信,苏显宗是苏米情绪失控下推下楼的。
我当时推苏显宗下楼时,戴了有苏米指纹的胶皮手套,我早有准备。
嘿。
而真正的苏米,早被我关地下室了。
案件“告破”,确认凶手是“苏米”之时,我会杀了真正的苏米,做成她“畏罪自杀”的假象,然后名正言顺,继承苏显宗和苏米的全部遗产。
当然,这遗产,我会分给配合我演戏的女医生 50%。
这是我的完美犯罪,无懈可击。
不过,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苏米被关在地下室,明明我都给她留了饭食和水,可她还是早早地死了,绝食,自杀。
这让我感到棘手。
她的死亡时间,和我计划里的死亡时间,对不上。
不过也没关系。
届时我会放一把火,将她的尸身烧成灰烬,烧到谁都看不出来。
自焚,不也是自杀的一种方式?
我站在原地,轻举酒杯,嘴角蔓延出了,一丝冷笑。
我的人生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肉眼可见地,我将拥有很多很多的钱。
我会走到阳光下,走到这,曾经让我觉得,我与周遭格格不入的,纷繁世界。
我将改头换面,像一个普通人那样,生活,或者做点小生意,平平安安,抑或庸庸碌碌。
我忽然想起地下室里,那些爬过我脚面的黑线鼠。
恍惚中,那些鼠又变成了我。
今晚的月光很凉,很亮。月亮圆圆的,就比那树梢高了一点点。
我举起酒杯。
宛若地窖里的老鼠,窥得那么一丝天光。
女医生睡醒了,慵懒着嗓子叫我,我喝了口酒去了。
约莫她是个重欲的人,我走过去的时候,她懒洋洋靠在床上,双腿交叠,见了我又分开。
缠绵时,她跟我叹说,那个女的(苏米)其实还挺可怜的。她推我肩膀挪谕我:“一个挺善良的姑娘,就这么给你毁了,你可真坏哦。”
我也是笑:“这世上善良人多,坏人也多,有时候都是命,怨不得谁。”
女医生叹说:“不过,我们也是作孽啊。”
我嗤笑:“怎么,你这样的人,突然大发慈悲,长出悲悯心了?”
女医生说,之前她为了配合我演戏,专程查了挺多苏米的资料,发现她真的是个挺善良的人,关爱老人小孩,捐款给希望工程,还捐款给红十字会,连蚂蚁森林都种了挺多树。八岁那年,她在路上看到一个奄奄一息的小男孩,都冒着被爸爸收拾的风险,将他带回家里,藏在地下室照顾了两个多月,直到搬家为止。
“多善良,”女医生说,“可惜了。”
她又瞟了我一眼:“多善良,可惜摊上了你。”
我身上的动作停了下来,我整个人硬邦邦的,冰雕一样,每动一下都能听到,骨头里咯吱咯吱地脆响。
苏米,是我找的那个姑娘吗?
我胸口就像是被一千根针扎了一下,疼得我双眼发黑。
我的眼睛像被人砸了重重一拳,疼得无奈闭上。
女医生笑说:“你这人真是作孽,要人家的钱也就算了,还要人家的心。有些人把钱看得重,有些人把情看得重。你说她好骗,无非是她把情看得重于一切。情分没了,也就什么都没了,所以活着没什么意思,不如死了重来。不过也没什么,反正你本来就是要灭口的。就是这杀人诛心,让我觉得她有点倒霉。”
我大脑嗡嗡的,就好像有风在我脑海里刮过一样,她后面的话我听不清。等我的思维从空白之处拾起时,她已经穿戴齐整了,坐在床上点烟,撩起眼皮,有些戏谑地看着我。
我像被针扎了一下,像头野兽一样扑过去掐她脖子。
好像找到一个暴力宣泄的出口,就足以抹平我所有的懊悔和愤怒。
在我失去理智,几乎要杀人的那一瞬间,警察破门而入。
而我就跟疯了一样,掐着她的脖子,死死不撒手。
即便两三个警察,抱着我的腰将我往后拖。
冷不防,一个尖锐的什么,刺中了我的胸口,我后退几步,不可思议地看着插在胸口的,我当年给苏米买的银簪。我手下意识地一摸,满手红彤彤的血。我颓然坐在地上。
而那女医生就跟变了个人一样,裹着衣裳连滚带爬溜到警察身边,整个人像是被吓坏了,凄凄惨惨哭着,一副梨花带雨的模样。
她指着我控诉:“警察叔叔,凶手是他!他杀了我爸爸,他想继承我爸的遗产!他还想杀我!他是职业骗子!他就是来骗婚的!你们查查就知道!他杀了我爸,还想让我帮他顶罪,让我装精神分裂,让我配合他表演,好让他脱罪!他 pua 我!他说只有这样,只有我帮他顶罪,他才能更爱我一点。我没想到,没想到他根本就不爱我,他只是想要我爸爸的钱,还想杀了我,伪装成畏罪自杀,然后继承我的遗产,呜呜呜,我这是作了什么孽啊,老天爷啊!呜呜呜!”
我坐在地上,看着自己一手的血。
脑子里懵懵的。
黑吃黑啊,这是。
女医生扎的这一下太准了,直接捅进了我心脏,就像是算计好了的一样,精准无比。
红色的血止不住,从我的胸口往外溅。很快,我全身开始发麻,手脚变得冰凉。
我想我大概是不行了。
玩鹰的人,却被鹰啄了眼睛。
也是该然。
我忽然有点想笑。
蒙眬中,我看见她居然过来扶我,以那样焦急的神情看着我,问我没事吧。
应该是装的吧。
我们都是职业骗子。
戴着同一张面具,用着同样虚伪的神情。
我攀住她胳膊,问她到底是谁。
是我找来的同行骗子,还是真正的苏米。
女人俯下身来,迎着我期待的目光,一寸寸地凑近我耳边,唇角上扬,一字一句:“你永远不可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