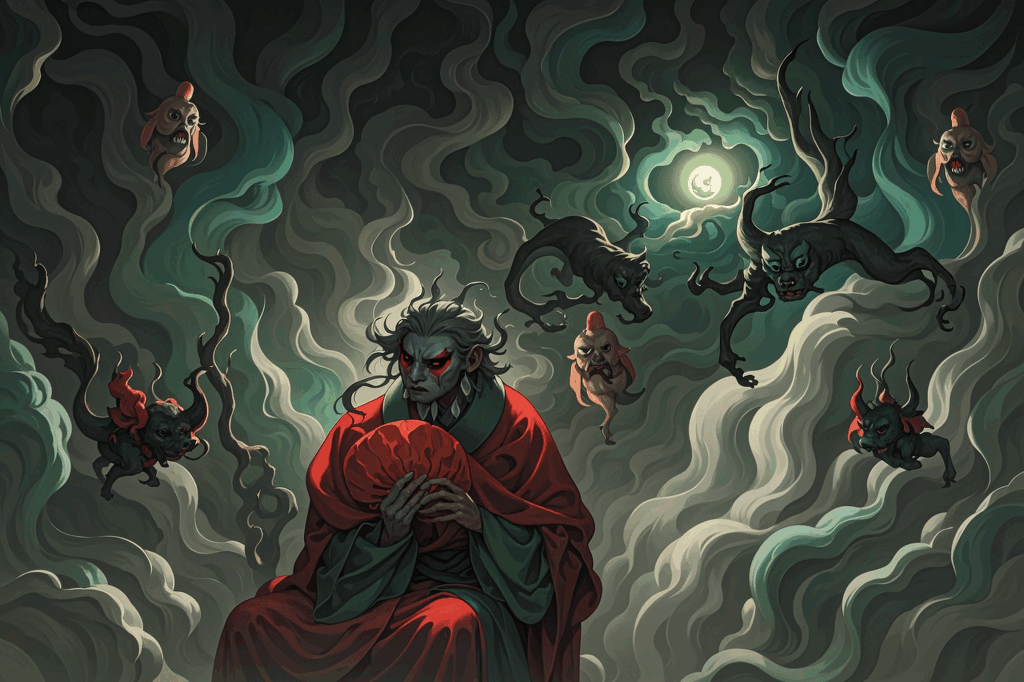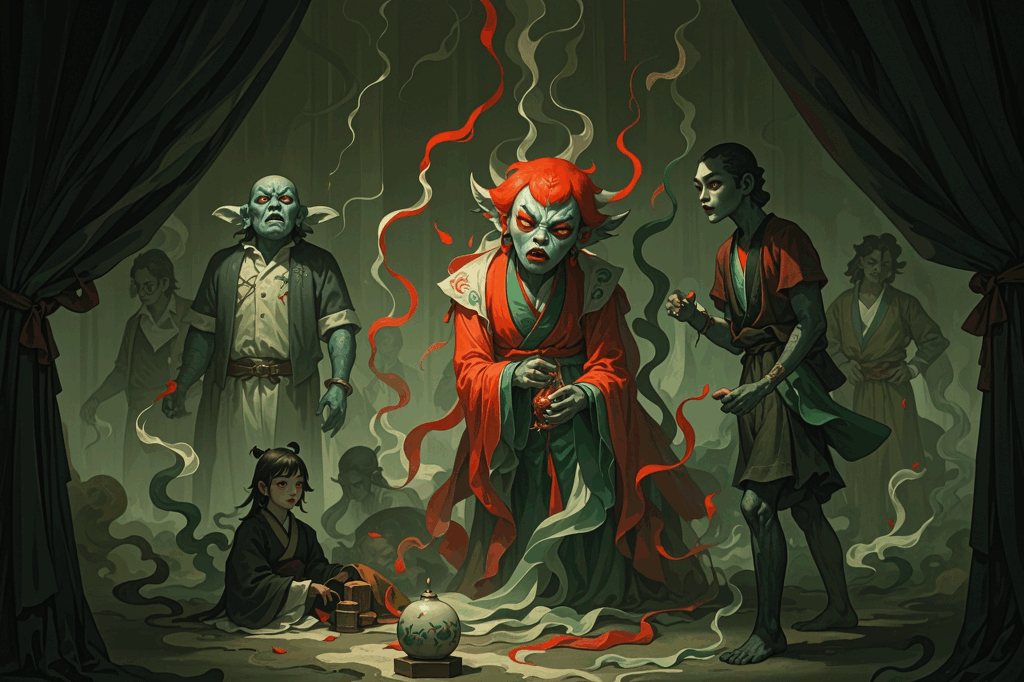小时候不懂大人的事,总觉得大人的世界很复杂。20年前,年仅10岁的我,没有读懂发生在我村的一个真实故事,今天重温这个故事,发现了赤裸裸的真相,令人黯然神伤,同时也令人不寒而栗!
首先说明,我并非养鸡专业户,对鸡也没有任何研究,只是这件事必须从鸡的身上开始讲起。当时,我村几乎每家每户都养牛、猪、鸡等牲畜,牛的住处叫“牛栏”,猪的住处叫“猪窦”,鸡的住处叫“鸡栅”。鸡栅一般是由竹片做成的一个长方体笼子,其中一边有个小门,供鸡出入,鸡栅放置在寨子里的上下大厅或者屋檐下等处。鸡的作息非常有规律,可以说,鸡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清晨啼叫(打卡),上午出栅(上班),傍晚入栅(下班)。可是,对于新四寨来说,从某一天开始,鸡的这种平静生活彻底被打破。
当时已经进入初冬,粤东的乡村显得有点寂静和寒冷,早上起来,家家户户屋顶的瓦片上积了一层白色的凝霜,人们说话时,口中喷出一阵浓浓的雾气。有一天,天刚蒙蒙亮,寨子里早起的厅婶大叫起来,说是她家的鸡被偷了。
有人偷鸡?这还了得!厅婶尖锐的叫喊声惊动了寨子中的人,左邻右舍纷纷起床了。有人连眼屎都还没有抹干净,有人外套还没披上,个个心焦火燎地走出来观望自家的鸡栅。还好,经过初步侦查,各家鸡栅完好无损,鸡一只不少。但温嫂家除外,因为她家并没有人及时起来检查。
看完数完自己家的鸡,大家都慢吞吞地来到厅婶家的鸡栅面前,细心的财伯对鸡栅进行了一番调查,发现鸡栅的其中两条竹子略微弯曲地拉向两边,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空隙。凝视了一会儿,财伯若有所思地说道:“厅婶,你家的鸡不是被人偷走的,应该是被狐狸之类的动物抓走的。你看看,鸡被抓住,然后从这缝隙中被生拉硬拽了出来。麻烦了,狐狸很有灵性,如果来抓过一次,以后肯定会顺着老路来的。”
众人听了,都觉得财伯的话很有道理。此时,离大厅不远处的一间房门打开了,温嫂走了出来,看她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应是刚从美梦中被吵醒,果然,她伸了伸懒腰,然后漫不经心地走了过来,问道:“怎么那么吵呀?”
厅婶立即走到她面前,对她说道:“快看看,狐狸吃鸡了,看你家的鸡是否也少了?”
可是,温嫂却没有丝毫的紧张,要知道,她的鸡栅可是摆放在厅婶的鸡栅的正对面呀,她的鸡栅和温嫂的鸡栅离寨子大门口最近,这些鸡可谓“同甘苦,共命运”,如果厅婶的鸡惨遭屠戮,温嫂的鸡也很难幸免。然而,温嫂走到自己家的鸡栅前,稍微一瞥就说道:“我家的鸡没有少!”
财伯听了,点头道:“没少就好。”突然,他看了看众人,眉头一皱,问道:“昨天晚上好像没有听到寨子里有什么动静呀。如果是狐狸来抓鸡,鸡栅里面的鸡肯定会有反应的,有人发现什么了吗?”
众人面面相觑,忽然,一个声音从温嫂的隔壁房间传了出来:“阿叔,我……听到了。”众人循声望去,竟然是典哥,于是众人唏嘘一声,并没有理会典哥,因为,他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傻子!然而,这个傻子非常不简单,经常说出惊人之语,让大家莫名其妙,而此时看他的样子,必有乾坤!
尽管众人对他置之不理,典哥还是愣头愣脑地走了过来,但是他的妻子温嫂却对他当头一击,挥着手向典哥说道:“哎呀,你懂什么呀?别过来添乱了,快回去,回去!”
大家不要怪温嫂对典哥态度粗鲁,因为她已经对着这样的典哥大约8年了,再温柔的女人也有点情绪,何况温嫂是一个不太简单的女人。但此时的典哥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被温嫂大声吆喝两句,就变成缩头乌龟,他径直走了过来,支支吾吾地对财伯说:“我……我……听见了!”
财伯望着说话结结巴巴的典哥,安慰道:“阿典,别急,你慢慢说。”
还是财伯善解人意,人家虽然是傻子,但傻子也是有尊严的,对不?何况多听几句话最多只是花点时间成本,而对于普通的庄稼汉来说,这并无大碍。得到了财伯的鼓励,典哥断断续续地说道:“我……我昨天晚上……很晚了,听到大门口有人说话和关大门的声音,然后有鸡叫声,就走了。”
根据典哥不太清晰的言语,大家依稀感觉到事情变得复杂起来:第一,有人说话,意味着有人来过,所以究竟是狐狸抓鸡还是人抓鸡,暂无定论;第二,关大门声、人说话声、鸡叫声,似乎寨子中并无其他人听到,为何傻子典哥却可以听到?
大家都静静地望着财伯,希望这位生活经验丰富的老人可以为众人释疑,但是,刚才还分析得头头是道的财伯也突然间变得满脸疑惑,或许,他有点相信堂侄典哥的话。此时,不知道谁在人群中无意地说道:“这就怪了,大家说说看,不会有鬼吧?”
其他人个个面带惧色,听了这个人的话,典哥似乎正中下怀,兴奋地点了点头:“嗯,嗯,有鬼!”
有人笑了起来。任何人提到鬼都好,但典哥不能提鬼,毕竟典哥的身份特殊嘛,他说有鬼,有人相信吗?还是财伯说话比较公道,他淡淡地说道:“有鬼没鬼,谁也不知道,我看大家还是商量一下,如何避免以后再发生这种情况吧。”
于是,新四寨的家长们个个绞尽脑汁,各抒己见,经过了半个多小时的讨论、论证、陈词,最后大家一致得出结论:为了避免以后家鸡失踪,晚上10点半钟后,由财伯关上正屋的大门,而寨子正屋另外一边的小门,由小门旁边那间房睡觉的陈叔婆在睡觉前顺便关上。注意,这个关上,不是掩上的意思,而是把里面的门闩也插上,这就意味着正堂里面的人出得去,但外面的人却进不来。还好,当时新四寨家中有电视的只有几户人家,并且都是放在非正屋的外面房间。另外,正屋里面的那些房子睡的都是老人和夫妻,而一般年轻人都在外面的房间睡,所以并无大碍。
毕竟这是为了众人的利益,大家都乐于接受,但是,肯定也会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如温嫂就提出了意见,她说如果晚上自己出去上茅厕,还没有回来就被其他人插上门闩,那岂不是很麻烦?
显然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很简单,谁出去,回来的时候顺便关上门就是了,其他人不要多管闲事去关门就好了。闹了半天,门还是关不死,但这多多少少能减少寨中人的担忧。
据后来新四寨的人传言,回家后,典哥受到了温嫂一番疾风骤雨般的训斥。可怜呀,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傻子,更让人痛彻心扉的是,据说,8年前的典哥根本就不是傻子,也就是说,典哥的“傻”,并非天生的,大家想想,如果天生就傻,温嫂还会那么愚蠢地嫁给一个傻子吗?这事,必须从8年前说起,唉,一言难尽,说来话长呀!
8年前,当然这还是个大约数,这样算来,当时我还是一个不懂世事的婴儿,并不能耳闻目睹或者用笔记录此事件。但是,这事流传甚广,深入民心,因为这件事足够诡异。下面这些文字就是我根据众人的传言整理的。
当时,正常人的典哥已经跟温嫂结婚3年,但是温嫂的肚子却始终不见变化,在当时来说,不孕是个难以启齿的问题,只有夫妻之间在被子底下谈论。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世俗的观念是恐怖的,于是在房前屋后,村子中的阿婆叔母的闲谈中多了一个话题。典哥夫妻俩在村民的流言飞语中熬日子,终于,他们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去县城逛街。奇妙的是,据说他们去县城逛街一次,回来后不久,温嫂就怀孕了。其实,去“逛街”是掩人耳目的说法,他们是去县人民医院看病。这样看来,科学技术确实发达,解决了典哥的大难题。一年之后,典哥家的幸福日子开始了,温嫂生下一女,非常可爱。按常理来说,在婴儿时期,每个小孩相貌都差不多,所以并没有大的风波。但是,一次偶然事件让典哥家从此不再平静。
当时,典哥家的家庭结构并不复杂,共四口人:夫妻俩,一岁多的女儿,年过六十的父亲森伯。一家人住在寨子正堂里面的两个房间里。有一个晚上,森伯外出大便,寨子外面漆黑。走出正堂屋,经过外面一排的房子时,看到自家另外一个闲杂房间窗户的空隙透出微弱的火光。森伯立刻警觉起来,因为他的老婆森婶在世时睡那间房,森婶过世之后,这里成了一个闲置的房间,不过里面偶尔铺床铺,供外来亲戚留宿什么的,但是此时三更半夜的,又没有亲戚留宿,有火光确实是太不正常了。森伯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来到那间房子门前,凑近门一听,更加怪异的事情出现了,他隐隐约约听到里面有女人的声音。森伯心头一惊:难道是死去的森婶显灵了?
站在房间门前的森伯凝视了片刻,镇定下来,毕竟是曾经相濡以沫的夫妻,即使是森婶贪恋人世、魂回故居,他也并不害怕。于是,森伯想推门进去,奇怪的是,门却推不开,这让他更加吃惊。农村人的像这种不常睡人的房间,外面一般不会上锁,里面如果没有人的话,更不可能锁上,但是为何却推不开?难道里面有人偷东西?这也太搞笑了,这样的一个房间有什么东西给人偷呢?森伯轻轻地拍了几下门框,同时低沉地呼唤:“喂,里面有人吗?”
房间里面出现一阵骚动,之后,迸出门缝的火光也立即熄灭。刹那间,房间里变得全无声息。森伯继续拍打,刚拍了两下,突然,两扇门“吱嘎”一声,打开了20厘米,从中间露出了一个脑袋,蓬头散发,脸部竟然看不清楚,森伯被吓了一大跳,本能地向后退了两步。
此人探出头来,用略带疲惫和气愤的声音说道:“爸,你三更半夜的来这里做什么呀?人家都睡觉了。”
凭借屋外朦胧的光线,森伯终于看清楚了儿媳妇红润的脸蛋,他的心跳终于平复下来,但心中又立刻产生了一个巨大疑问。
森伯疑惑地问道:“怎么是你?好好的,你怎么跑到这个房间来睡了?”
温嫂打了个哈欠,有气无力地说道:“爸,这还用说,我们吵架了!”
森伯沉默了,确实,典哥夫妻两个磕磕碰碰还是有的,偶尔的吵架也再正常不过。不过森伯感觉到,此次的吵架非同小可,农村的夫妻吵架都是床头吵架床尾和,哪有媳妇生这么大的气,闹什么分房而睡呢?
温嫂打破沉默,说道:“爸,都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你也不要去说阿典,过两天我们就没事。”说完,温嫂就关上了门。森伯这才想起来,自己本来要去大便的,于是急急忙忙走出了大门,朝茅厕跑去。
10分钟后,森伯方便完毕,然后摸着黑慢慢朝寨子的大坪走。正要进入寨子的大门时,森伯在黑暗中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从寨子的大门口溜了出去,虽说此时的森伯上了年纪,但并非老眼昏花,据说,根据此人的身材,他大概知道了是谁。但是此人究竟从谁的家里走出,森伯却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当他走进寨子里,并没有见到寨子中哪一户人家还有灯光。此时的森伯做梦也没有想到,此人竟然跟自己的家庭有关。
第二天,温嫂去河边洗衣服,森伯找来了典哥,问及吵架的事情。可是,典哥感到莫名其妙,他根本不知道父亲具体讲哪件事情。森伯详细说明情况后,典哥恍然大悟说道:“爸,我明白了,可能是昨天晚上就菜的咸淡问题我说了一下她,她之后就闷闷不乐,可能因为这事呢。”
森伯说出了掩藏在他内心深处的忧虑,他严肃地对典哥说:“阿典,这怎么可能,就因为这么小的事,你们分房睡?”
典哥彻底糊涂了,他疑惑地望着自己的父亲,那双眼睛显得特别单纯,他战战兢兢地问道:“爸,你说什么?我不懂你的意思,什么分房睡觉?”
森伯被儿子搞糊涂了,他不知道儿子是真糊涂还是假装糊涂,但知子莫如父,自从森婶过世后,没有人比他更关心典哥,他迫不及待地问典哥:“阿典,难道你不知道昨天晚上你老婆去外屋睡吗?”
典哥顿时脸色大变,急忙辩解道:“爸,不可能啊,昨天晚上一起上床,早上起来时,她还比我晚起床呢!”说完,典哥望着苍老的父亲,森伯也默然地看着善良的儿子,他们两个就这样沉默着,或许,他们两个都知道了大概怎么回事。
但这一切都是怀疑,要消除怀疑,得到真相,就必须暗中进行周密的调查,可是这谈何容易。有些事情,少则几分钟,多则半小时,心思缜密的人完全有可能在晚上起来声称外出大便而成就苟且之事。太可怕了,森伯不敢往下想,但他是一家之长,他是男人,又是父亲,有责任去维护这个家庭的团结和稳定,更有责任在一点点线索之中找出那个可恶媳妇的破绽。
本来还心存一丝侥幸,但森伯的细心让自己的幻想彻底覆灭。据说森伯跟儿子都是抽烟丝的,当时农村的烟民都是如此操作:抓点烟丝,用一小块白纸卷起来。森伯在打扫空置房间时,竟然无意中发现了一颗烟头,是梅州烟嘴。毋庸置疑,确实是有外人来过,此时,森伯比自己的儿子还痛苦,或许儿子还蒙在鼓里,但他自己却在那一瞬间心如明镜。可是,悲哀的是,此时的森伯并不清楚,儿子也有过错,因为儿子的身体存在缺陷!无论如何,偷情这个事情,毕竟有个偷字,即使不算盗窃罪,世人那鄙夷的眼光也会把你烧死,那唾沫星子也会把你淹死。
于是,森伯有意识地进行了布控、排查。在那个月朗星稀的夜晚,森伯独自一人开展了一次抓奸活动。
据说,当时的典哥去外村做零工了,要在外村过夜!平日里疑心重重的森伯料定当天晚上会出事,于是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早早地睡了。当然这一切都只是个假象,他只是躺在床上,耐心地等待外面的动静。毕竟,抓奸可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当时可没有偷拍、监控、请侦探公司之类的玩意儿,一切都要自己亲力亲为,真是难为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时间不知不觉来到半夜,突然间,他听到屋子的门前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随后隔壁传来了开门声。森伯觉得时机成熟了,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拿起早已准备好的工具,轻轻地打开自己的房门,轻轻地挪动着步子来到儿子的房前。
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森伯把耳朵凑近门前,果然听到媳妇在房间里面跟人窃窃私语,具体说什么无法听清,不过他敢肯定的是,他们是在为干那事做准备,于是一项伟大的捉奸活动按照原定的计划悄然进行。森伯重重地拍了一下门,同时装作痛苦地喊道:“阿娣(温嫂名)……快开门……我肚子痛,我恐怕不行了。”房间内立即传来了下床的声音,然后听到匆忙的脚步声,离房门越来越近,接着门立即被打开,在暗淡的灯光下,森伯看到了儿媳妇那张无耻的脸。温嫂却关切地问道:“爸,你怎么了?”
森伯立即闪进了房间,森伯装出的痛苦的呻吟声也戛然而止,他走向了床边。据说,就在森伯走过温嫂身边的时候,温嫂看到森伯藏在后背的那只手拿了一把明晃晃的镰刀,温嫂感到事情不妙,她脸色大变,胆战心惊地问道:“爸……爸……你这是怎么了?你要干什么?”
森伯并没有说话,走到了床沿。温嫂以为公公发疯了,要杀孙女,立即尖叫一声:“不要!”正是这一句“不要”更加让森伯相信自己的判断,“不要”是为奸夫讨饶,为奸夫求情,为奸夫乞怜,这太可恶了,森伯怒气冲冲地把镰刀举了起来,狠狠地朝着被子砍了下去。但是,被子里面没有发出一丝声响,难道奸夫被自己一刀砍死了?不,没有那么容易死的,死了也好,奸夫淫妇被世人唾弃,说出去自己也是对的,要死就彻底地死去吧。镰刀再次被举了起来,又砍了下去,此刻,被子中的棉花裸露出来。温嫂早已吓得目瞪口呆,但是,血浓于水呀,她在关键时刻作出了明智的决定,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温嫂疯狂地跑到床边,把上面盖着的被子掀到床下,一把把弱小的女儿抱在怀里,紧紧地抱在怀里,一句话也没有说。森伯看到床空荡荡的,仍没有死心,他杀气腾腾地走到床前。
不,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肯定是在哪里藏起来了。反正今天撕破脸皮,不成功,便成仁,一定要在这2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搜出奸夫。当晚,森伯算是豁出去了,他满脸杀气,从头到尾没有叫嚷一句。森伯立即蹲了下来,朝床底看了看,也是一无所获,门角、桌下等地方都搜了一遍,仍然没有收获。
此时温嫂已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她终于缓过神来,抱着女儿凶巴巴地质问森伯:“你这个死老鬼,你究竟想干什么?”
森伯回过头来,横眉怒目地看着温嫂,冷冷地说道:“你还有脸问我?你自己做的事情,自己心里清楚。”
温嫂底气十足,毫不畏惧,恶狠狠地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有本事就把我们母女砍死。”
森伯冷冷地说:“我杀你们干什么!我要杀火狗!”
就在“火狗”这两个字从森伯口中迸出来的时候,温嫂大吃一惊,脸色骤变,然后抱着女儿慢慢地走向床沿,一声不吭地坐了下来。森伯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虽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但在我村的抓奸史上意义重大:第一,打击了奸夫淫妇的嚣张气势:第二,对树立我村良好民风、共建和谐的乡村生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天晚上,传说中的那个爽歪歪的火狗并没有在现场出现。森伯和儿媳妇对峙了一阵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比较平静的争吵。一些聆听的好事者把他们隐隐约约的对话总结如下:温嫂的话大概意思是,如果我不这样,你们家就绝种;而森伯的话大概意思是,这样的绝种是光荣的绝种,我宁愿绝种,也不要你这样伤风败俗,丢尽脸面。但是,话又说回来,这是个严峻的问题,是个令人痛苦不堪的问题。
根据听到当晚风声的人士分析和之后森伯家庭的走向,村民可以知道,森伯以“家丑不外扬”为宗旨,对温嫂既往不咎,当然,温嫂也绝不能再犯错误。但是,温嫂犯不犯错误,取决于森伯这个有威严的一家之主。如果森伯过世,没了忌惮,谁也不能保证温嫂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不出现任何差错。
果然,一年后,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或许因打击沉重,或许因农活劳累,森伯在此事之后病倒了。正所谓“祸不单行”,在父亲病倒之后不久,典哥彻底地疯了。据说,典哥变疯的过程非常诡异。各种传言中,广为流传的版本是:
正常的典哥跟着步履蹒跚的父亲去一座比较远的公山找草药。公山嘛,料想山中结构比较复杂,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怪物。典哥看到了长在偏僻处的奇花异草,森伯对他说,这是有用的草药,叫典哥过去割一点回去。
可是,正常的典哥走了过去,却再也没有正常地回来!
走过去的典哥,把那把草割了下来,却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背对着森伯,森伯看到典哥有些怪异,喊道:“阿典,你怎么了?”但是此时的典哥却毫无反应。
好奇的森伯艰难地走了过去,发现典哥站立在一副破旧的棺材之上,而这簇花草恰好是长在棺材上,经过长年累月的风吹雨打,棺材早已腐朽。森伯惊呆了,因为凭着他的经验,这肯定是一个无人收拾的墓地,森伯歇斯底里地大喊:“阿典,快走!阿典,快走!”
典哥根本没有移动脚步,艰难地扭过头,露出一丝古怪的微笑,沉吟道:“爸,我走不了!”
森伯拼命地喊着典哥的名字,立即走到典哥的面前,扇了典哥两巴掌。突然,典哥“嘻嘻嘻”地笑了起来。森伯大吼道:“快走呀,快走呀!”
见典哥对自己的吼声充耳不闻,森伯急中生智,伸手把典哥的手用力一拉,典哥硬邦邦地倒下来,压在森伯的身上。典哥的脚仍然无法脱离棺材,棺材盖也随着他的脚被掀了开来,顿时,空气中充斥着一种怪异的味道,呛得森伯咳嗽了几下。被典哥压倒的森伯挣扎起身,发现典哥脚上穿的解放鞋粘着棺材盖,棺材盖上流淌着一种乳白色的液体,导致典哥无法挣脱棺材盖的束缚,森伯立即走了过去,把典哥鞋子上的鞋带解开。此时,森伯感觉到一个高大的影子从废弃棺材中慢慢站起,朝自己挪过来。森伯吓得魂飞魄散,背着典哥拼命逃跑,根本无暇顾及后面那个影子是否跟着。
森伯背着典哥回来后,寨中人个个惊呆了。后来即使全村的老人到场,都不知道那副棺材究竟是谁的,但也有人在私下说,森伯是在制造谣言,无中生有!
不管森伯是否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反正村民从那一刻形成共识—被无名鬼惊吓,典哥疯了。经过了神棍曾开的一番驱鬼除魔作法,典哥的病症似乎有所缓解,但在村民的眼中,他成了“半桶水”、“少阵火”、“不足水”等的代名词。
就在典哥变得不正常之后不久,森伯开始变得气息微弱,可是,这个伟大的父亲还是留下了两口气交代后事。
第一口气是留给财伯的。财伯是森伯的堂弟,森伯的大概意思是,自己死后,要财伯多照看一下傻子阿典,如果典哥的媳妇以后做了对不起典哥的事情,森伯做鬼也不会放过温嫂的。不过,森伯还是希望身边的亲戚多对温嫂旁敲侧击,希望温嫂能够勤俭持家,跟典哥生活下去。
第二口气留给了典哥。或许是典哥是傻子的缘故,他们的沟通并没有用太多的言语,森伯指了指放在门角处自己平时用过的那把镰刀,典哥会意地点了点头,一切尽在不言中。指示宣布完毕,森伯正式宣告死亡!
森伯死后,典哥让人佩服的是,3年之内,家中再添两个新丁—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典哥一直带着根本不像自己的大女儿在一个房间睡,温嫂带着两个小孩在另外一个房间睡,平静的生活一直持续着,直到这次偷鸡事件,一切才算终结!
自从新四寨中实行关门政策之后,寨子里风平浪静。但是,偷鸡事情很快告破,结果却让寨子中人大跌眼镜。
据屋子处于最后围的壁婶叙述,她家这几天以来充斥了异味,由刚开始的浅淡,到后来的臭气熏天,令人难以忍受。他们猜想肯定是死了什么东西,首先怀疑家中有死老鼠,但是,一家人翻箱倒柜,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却没有找到,最后还是站在窗户边的小女儿发现,臭气根本不是从自家中发出的,而是从窗户外面吹进来的。壁婶的屋子窗户外面不远处是后山。于是,壁婶的家人从大门走出,来到后山,发现自家的窗户对面的后山上有一只死鸡,已经全身腐烂不堪,臭气难闻。
顿时,寨中哗然,从这个迹象看来,厅婶的鸡失踪,不是偷鸡贼干的,而是狡猾的狐狸干的。不管是人还是狐狸,关门无疑是个上上之策。就在寨子里实施关门措施之后不久,“狐狸”还是按捺不住偷吃家禽的欲望,又在蠢蠢欲动。
等的就是你,来吧,狐狸,我们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只要你敢闯进我们的寨子顶风作案,你就等于自投罗网,到时我们关门打狗也好,请君入瓮也好,必须让事情有个了断。
那天晚上,寨子里寂静无声,子夜悄然来临。据后来确认,在这一刻起码有3种生灵出动,第一种是猎物,第二种是猎人,第三种是引导者。而引导者尤其恐怖,根据迹象可知,引导者竟然是死去的森伯。当时第一个听到寨子里动静的人是在小门口睡觉的陈叔婆,她听到门被什么东西撞击的声音。这位老人家还是比较有责任心的,立即摸黑起床,走出小门,却发现小门关闭完好,她立即打开了小门,向外张望,外面漆黑一团。但是,就在此时,一个矮小的东西从她脚下闯了进来,陈叔婆心里一惊,知道是狐狸钻进来了。她转身看到这只小动物沿着屋檐飞快地躲进了典哥家的浴室,陈叔婆立即跑到大门旁边的房间,叫醒了财伯,第一时间向财伯汇报情况。
财伯顿时精神抖擞,叫醒了在隔壁房间睡觉的毕叔。毕竟当时夜深人静,兴师动众也不太好,料想两个男人已经足够对付,于是,他们两人各拿了一根带尖头的铁棍,走了过来。在陈叔婆的指引下,他们3人一起来到典哥家的浴室前的不远处,果然听到浴室里面传来微弱的声音。
但是,这声音非常古怪,似乎有人在谈话,夹杂着金属敲击的声音,3人都狐疑起来,财伯脸色格外凝重,他示意年纪稍小的毕叔走在前面。在幽暗的灯光下,毕叔的脸色显得非常难看。半夜的天气有点冷,尽管寨子里的大小门都严实地关闭着,但是天井处仍是露天的,偶尔可以听到后山的树木被风吹得簌簌作响。
毕叔一人走了过去,来到浴室面前,却发现浴室门被关上了。还好,浴室门并不是密不透风的,而是由几块木板简单地钉成的一块门框,所以可以说是四处通风,刚好毕叔个子比较高,站在浴室的门框前,黑灯瞎火之中,他把头从门框上伸了进去。
可是,几秒钟之后,毕叔把头缩了回来,并且快速地往后退,此时,在不远处站着的财伯,凭借微弱的光线,看到毕叔的脸上露出不同寻常的恐惧表情。毕叔飞快地走到财伯的旁边,指了指浴室,紧张地说道:“是阿典!”
阿典?森伯立即把毕叔拉到了旁边,小声地问道:“怎么会是阿典?他在里面干什么?”
毕叔心有余悸地说道:“不知道干什么,我刚才伸头进去,他好像根本没有理会,我看到他正全神贯注地盯着浴室墙壁上挂着的刀卡。”
财伯还没有反应过来,突然,浴室门被悄无声息地打开,典哥走了出来,他手里握着一把镰刀,镰刀在这黑夜里显得异常模糊。财伯和毕叔都愣住了。让人觉得奇怪的是,从光线和角度来看,典哥应该可以看到他们几个人,但他根本没有朝这边看,而是一步步地沿着屋檐走去,就如梦游一般。
财伯想走过去,但是被毕叔拉住了,毕叔压低嗓门说道:“财哥,财哥,你别过去,阿典手上有镰刀,危险!”
财伯从毕叔的拉扯中挣脱了,他相信,阿典不会对自己的堂叔下手。财伯走了过去,此时,阿典竟然停止了脚步,但并没有回头看财伯。财伯在典哥身后战战兢兢地对典哥说:“阿典,我是你财叔呀,你这是怎么了?”
典哥慢慢地回过头,据说,此时的典哥,面无血色,目露凶光,见到财伯,也没有感到丝毫的惊讶,愣了愣,说出了一个让财伯无法理解的字:“爸!”
就在这一刹那,一只白色的动物出现在浴室门口,然后动作迅猛地跑到温嫂睡觉的那个房间前,而此时,那边同时出现了3个身影,追了过来,那只动物走投无路,却从窗户的空隙中钻进了温嫂睡觉的房间。那边的3人走了过来,原来是寨子中人,每个人都拿着一条扁担,其中一人惊讶且低声地问道:“财伯,你怎么也在这儿?也是来抓狐狸的?”
财伯点了点头,问道:“狐狸呢?”
那人指了指了温嫂的那间睡房,财伯和毕叔都感到非常诧异,那团如火光的动物竟然是狐狸?
此时,另外几人焦急地问:“财伯,怎么办?狐狸躲进房间里去了,如果打开门,然后关门搜寻,狐狸肯定在劫难逃,但这三更半夜的,怎么可以闯进去呢?”财伯示意大家说话不要那么大声,毕竟寨子中的人大部分已经熟睡,财伯皱起眉头,思考有什么万全之策。此时,典哥面目狰狞地握着镰刀从财伯身边走过,像一个冷血杀手,在温嫂的睡房门前站住。
其他人都知道,那是典哥的家,他叫醒老婆让众人抓狐狸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于是大家摩拳擦掌,等待典哥叫开门,好拿起家伙打狐狸。但是,让在场所有人感到惊讶的是,典哥根本没有敲门,在朦胧的光线下,他非常娴熟地把镰刀从两扇门的门缝中竖向插了进去,向下用力一钩,门闩被打开了,然后推门进去。就在门响的一瞬间,睡房里面发出一阵尖叫,这是男人和女人惊恐的尖叫。站在屋檐下的众人并没有立即闯进去,而是在门口等待,因为这是别人的睡房,财伯在关键时刻大声吆喝:“快进去抓狐狸呀,还等什么?别让它跑了啊!”
众人听了,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跑进了房间,可是房间内黑不溜秋,在瞬间根本无法看到什么。财伯大喊一声:“关门,别让狐狸跑了!”门立即被关闭起来。
典哥轻手熟路地走向房间门口旁边的开关处,拉开了灯闸,灯光亮了起来!
顿时,房间里明如白昼!离床不远的地方站着5个男人、一个女人(陈叔婆),如列队观望,个个瞠目结舌。典哥站在床前,手里摇动着明晃晃的镰刀。
床上,有两个成年人,毫无疑问,其中有一个是房间的女主人,但另外一个男人,却不是传说中的“火狗”,看来温嫂真是强啊,不只有一个姘夫!此时,温嫂吓得浑身发抖,用双手拉着被子盖在自己身上,缩在床上一角里的男人早已吓得面无血色。毕竟这不是色情片拍摄现场呀,那么多观众,如何面对哦。典哥毫不含糊,大声吼道:“起来!”这时候,外面几个寨子中的人都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掩面想开门出去。财伯大吼道:“大家都别走,我们是来抓狐狸的,怕什么?今晚就让大家见证一下,谁是真正的‘狐狸’。”
床上的男人,不知道是不是被吓糊涂了,并没有起来。典哥终于忍无可忍,高举镰刀,砍了下去!
典哥的镰刀砍在支撑蚊帐的床棍上,整个蚊帐倒塌下来,典哥大声吼道:“还不起来是吗?再不起来老子砍死你!”据说,典哥的声音毫不含糊,男子汉气概十足,此时他的脑子再正常不过。
这男人哆哆嗦嗦地起床了,据说起来后身子光溜溜的,还想穿衣服,典哥吆喝一声:“还穿什么衣服,滚,滚,滚!”
这男人在慌张中抓了自己的衣服,在众目睽睽之下打开房门,离开典哥的寨子,朝村尾的家中奔去……因为这不是好事,所以在此并不指名道姓,连化名也免了。
那男人走后,大家才意识到进到这个房间原本是来抓狐狸的,却演变成一场意外的抓奸活动,早把抓狐狸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说来也奇怪,当现场所有人都沉浸在诧异中时,突然,一个像是动物的东西从门角闪电般逃了出去!
财伯大喊:“快追!”众人都拿着工具追了出去。
但狐狸根本没有抓到,有人说,那不是一只狐狸,而是一个引路的魂魄。如果真是这样,料想大家也知道那是谁的魂魄了。
温嫂的奸情终于大白于天下,并且被5个男人误打误撞当场识破。或许这个打击对她来说太沉重了,或许这件事在她心灵上留下了严重的创伤,从此她很少在众人面前说话。她还是贪恋人世间的七情六欲,没有勇气自尽,苟活了下来。因为说话少,沟通少,她逐渐变得呆头呆脑起来,更让村民无法相信的是,典哥反而越来越正常。
终于,温嫂过度地透支了她的青春,郁郁寡欢的她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有人说这种病对于她来说,并非上天过分,而是“自作孽,不可活”!以前村民说这病时讳莫如深,其实按照今天的医学说法,它叫“宫颈癌”。后来病情逐渐恶化,不久温嫂就病死了。其实,想起来这病的由来一点也不古怪,毕竟曾经的偷鸡摸狗是在偷偷摸摸中进行,因此不洁性生活造成了她的可悲结局。
后来,有人传言,典哥的脑子从来都没有不正常过,因为我村村民并没有找到他曾经发疯的那个现场。棺材之类的鬼话,也许不过是典哥无可奈何且用心良苦的策划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