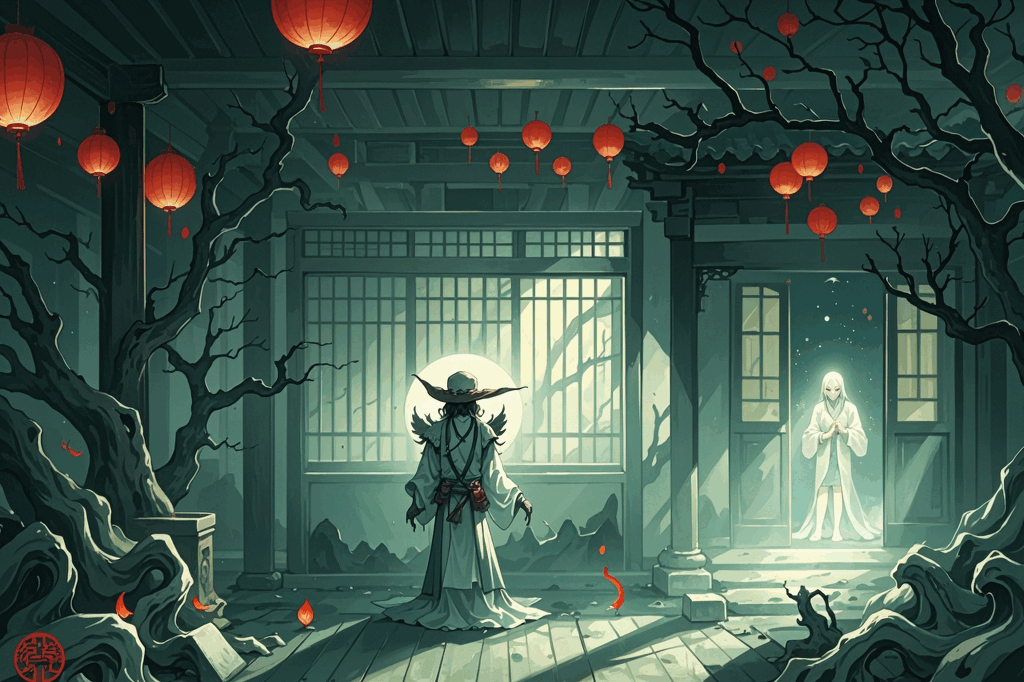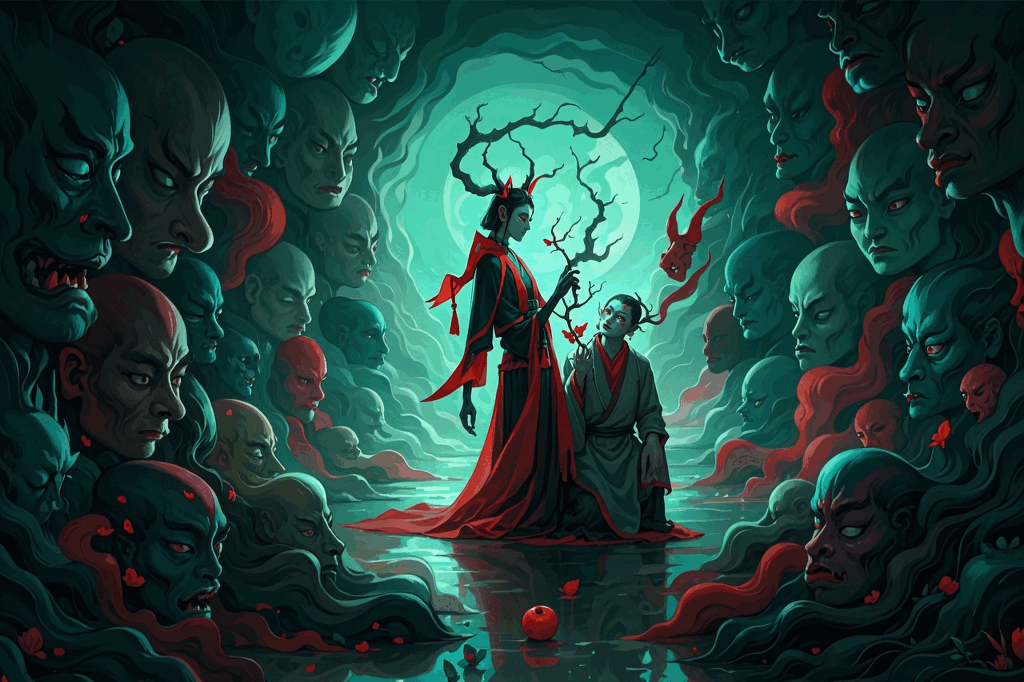20世纪90年代初,第一批外地山工开始陆续进驻我村,为我村的林木开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山工,主要有两个大派系—湖南派和江西派,每个派系又分出一个个小团队,分别驻扎在我村的各个寨子。这些山工长年累月居住我村,有一部分人到最后离开时,竟然可以说一口流利的客家话,可以说客家风俗对他们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但是,对鬼神的认知程度,部分山工跟我村村民却不尽相同。
仲春的某天,一个青壮男人,引着两个更为年轻的小伙和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在我村村民的指引下来到村长之家。根据他们所带的行李,村长一眼就知道是来我村做山工的,于是热情地招呼他们。首先要安顿他们的住处,于是村长带着他们四个找到了住在另外一个寨子的我家。
村长来到我家门口,当时我妈在家中,村长大大咧咧地说:“你家不是有空置的房子吗?租给这几个江西人住吧。”我妈迟疑片刻,说:“我家哪里有多余的房子呀?刚好够住呢。”
村长从门口稍微走出去一点,然后指着我家的上堂房子,不屑一顾地说道:“那间不是吗?南哥搬走了,他家的房子不就是由你家接管吗?租给他们,价钱我来定。”
我妈听了村长的话,左右为难,见那几个江西人就在旁边默默地看着,于是就叫村长到走廊的尽头,压低嗓门说:“村长呀,你也知道,那房子是南哥家的——”
村长打断我妈的话:“那又怎么样?你呀,不要跟我说迷信的东西。”说完,走到江西人旁边,对领头的那个青壮男人笑道:“她说那房子以前住过老人,你们敢住吗?”
四位江西人听了都愣了一下,其中,年过半百的老头摇了摇头,说:“还是另外找过吧。”
“不,”青壮男人打断了他的话,“租吧,出门在外,什么都怕,还赚什么钱嘛!”
看着领头的人说得这么淡定,村长也就极力地推荐。我妈碍于村长的面子,极不情愿地把房子租给了这几个江西人,接着就收拾房子里面的东西,最后郑重其事地对他们说道:“房子上的二楼(木棚)放置了一些东西,是原来房子主人留下来的,具体是什么,我也不清楚,请你们不要动。”
领头的人也客客气气地说:“知道了。”于是,这几个江西人就在我寨驻扎下来,山工生活也正式开始。
一个周末,念初中的我回到家中,晚饭之后,来到上堂与下堂之间的侧房复习功课,这个房间是我的书房兼睡房。晚上10点左右,我悄悄溜出房间。屋外一片漆黑,仲春之夜,还略带凉意,让人备感舒适。我从走廊摸黑走到上堂门前,见上堂屋子房门半掩着,房间内灯泡发出的淡黄色灯光有点昏沉,里面悄无声息。
我屏住呼吸,把头伸进门缝,看到房间里床上的被子隆起,中间似乎躺着一个人,由于角度问题,看不到别的。就在我静悄悄地观察房间时,门突然“吱嘎”一声打开来,一个人影直立在我面前,吓了我一大跳。
“是你呀,快进来坐。”显然这位江西老表知道我是房东的儿子。我本来也是喜欢热闹的人,于是就进入房间跟他闲聊起来。在闲聊中得知,他们四人来自江西省定南县,他叫钟二,在床上睡觉的叫钟大,是他的同胞哥哥,二楼木棚上面睡的是一对父子。
虽说我与他初次闲聊,但是彼此无所不谈。原来钟二比当时的我只大了两三岁而已,因家境贫寒,早早辍学,来到我村做山工。但他对未来抱有很大的憧憬,放在他桌面上的书籍就是很好的证明,在我进来房间之前,其他人都已休息,他却独自一人专心致志地在看书。
大概过了半小时,钟大仍在床上睡觉,一动不动的,而二楼木棚上的那对父子估计也已进入梦乡。突然,一阵阴风吹过,木制的窗户竟然被吹开了,屋内在半空中吊着的灯泡也晃动起来,投射到地面上的影子飘忽不定。当时的我并没有多想,然而回过头来我却发现钟二那惊魂不定的表情,他似乎走了神。
我颇觉奇怪,忙问道:“钟二,你怎么啦?”
他回过神来,支支吾吾地说:“曾江,你不要说话!”
我被钟二突如其来的严肃搞得莫名其妙。钟二把他那呆滞的目光投向了那张床—钟大睡的床。让人觉得诧异的是,一直在床上酣睡的钟大,似乎也有所动作。只见钟大的上半身纹丝不动,而脚却在挣扎,因为脚这边的被子一阵阵地被踢起,从刚开始的轻柔,变得剧烈。钟大的呼吸声音也逐渐变粗,非常急促,上气不接下气似的,应该是非常难受。
此时坐在我旁边的钟二急得似乎要哭了,突然他跑到钟大的旁边,把盖在钟大上面的被子用力掀开,然后用手抓着钟大的双臂,用尽全力地摇动,焦急地说:“大哥,你醒醒!”
在被子被钟二掀开的同时,我看到了钟大令人疑惑的姿势:他的两只脚摆放得笔直,呈八字形地微微张开,就如体育课立定一样,只是我们是站着,而他是躺着。
作为一个看客的我,一时间不知所措。而伴随着钟二的尖叫声,楼上的两父子也从棚上下来了,做父亲的可能是工作辛苦的缘故,看起来很沧桑。只见他不慌不忙地走到床旁边,示意钟二走开,然后他不动声色地搂住了钟大的脖子,将双手平行地伸进钟大的背部,也不知道他在钟大的背部做了什么动作,只见原本耷拉着脑袋且两眼紧闭的钟大突然间眼睛大睁,清醒了过来。
只见钟大大汗淋漓,衣服几乎湿透,足以表明他刚刚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战斗”。然而,这位中老年人却叫钟大别说话,只是坐在床边,叫钟二倒了一大杯白开水,让钟大喝了下去,然后叫他平躺在床上,好好休息!
见钟大平安无事,我的心情也趋于平和,毕竟这是我们村子的地盘,如果他们有什么三长两短,作为东道主的我们,多多少少是有点责任的。同时,我感觉到这位中老年人应该是个医术高明的医生,即使不是,他也是个生活常识非常丰富的人。可是,他却不明白,医生最大的痛苦是他医好了无数的病人,却医不好自己;至少,在我们的村子里,或者说在这个屋子里,他没有医好自己。
见钟大需要好好休息,我也不便打扰,于是回去睡觉。
到了第二天,我把昨天晚上在上堂房子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妈。我妈听后,脸色大变,过了好久,自言自语道:“没事,没事,房子有人住,更有气息,怎么会怪罪呢?这样是帮他家看管房子啊。”妈妈的话让我听得一头雾水。当天上午,趁着江西人出发上山后,我妈走到上堂门口,烧了香,嘴里絮絮叨叨地念些什么,大概意思是你要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怎么的,要保护什么的。见我妈的行为如此诡异,我似乎也意识到什么,难道鬼真的存在?还好,之后的一个星期,大家平安无事。
又是一个周末,我特地找他们闲聊,正所谓“一回生,二回熟”嘛。我故意开玩笑讲起那天晚上发生在钟大身上那件诡异的事情。此时的钟大已经无所顾忌,大声说道:“其实,那是鬼上身,他妈的,看它以后还敢不敢来,我砍死它。”
钟大说得龇牙咧嘴,毫不在意,钟二却露出不安的神情,对钟大说道:“哥,你少说两句不行吗?这玩意儿,是可以开玩笑的吗?”
钟大听了钟二的话,并没有丝毫收敛,相反,他笑得前仰后合:“哈哈,我就是要说,看它下次来,我砍死它,让它永世不得超生,哈哈。”
钟二脸色非常难看,痛恨他哥哥的大言不惭,不过他也没有法子。看来,钟大跟当时的我也算是同道中人,他敢如此宣言,应该也是个无神论者,绝对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会存在鬼的。即使他相信鬼神之说,对于如何去制伏鬼肯定也是心中有数。不然他怎么会如此大胆,竟然在别人的地盘上如此理直气壮地说话?后来,事实证明,钟大确实是条好汉!
接着,他对我说道:“曾江,你们家不跟我明说,我也知道,这房间肯定是不干净的。上次嘛,我还以为是做梦,感觉一个穿着黑衣棉袄、头戴黑色毡帽的老者过来掐我,我的意识是清醒的,就是被他掐住了,无法动弹,当时你也看到了嘛。不过当时的我没有准备,不然……呵呵,以后都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
听了钟大的话,我觉得非常好奇,为什么以后不会发生?从他的话语里我猜测:一、钟大确实是遇到那东西了;二、钟大是个类似于神棍的人物,或许他心中已有锦囊妙计对付不干净的东西。但事后证明,钟大悲剧的产生多多少少跟他这种盲目自信有关。
就在钟大大话连篇的当晚,上堂的屋里似乎发生了很大的动静。当时,整个寨子里只有三户人家有电视,都在外围的房子里,一般情况,晚上黄金时间段大多数人都跑去看电视了。这四位江西老表在他们紧张的工作之余,也会去那里凑凑热闹,但那天晚上,他们四人中,去看电视的有三人,唯独钟大没有去。
我的睡房靠近走廊这边是没有窗户的,我一直关着门在房间里看书,不知道那天晚上外面有多黑。大概晚上9点,寂静的正堂屋里没有一丝声响,在这种情况下,外面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尽在我的掌控之中。
正在我对一道“全等三角形”的证明题冥思苦想时,突然,从上堂房间里传出钟大的一声大喊:“来了!”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
糟糕,会不会钟大出事了?如果又出现上次的情况,又没有人在他身边的话,那钟大会不会死掉?我要不要走出去看看?不能!太危险了,因为钟大白天的话和我妈之前的奇怪行为,都让我慢慢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中。我开始坐立不安起来,无心再研究“全等三角形”还是“相似三角形”了,离开座位,关了灯,蹑手蹑脚靠近门缝,倾听着外面的一切动静。
可惜,因为方向问题,我根本无法窥视到上堂的房子,从房间的门缝看,外面漆黑一团。我轻轻地走回来坐在椅子上,心里忐忑不安。大概过了三分钟,终于听到钟大的声音了,他咆哮起来:“来呀,再来呀!”钟大的声音听起来有点亢奋,但同时也有点颤抖。
我再次来到门边,偷偷地把门微微打开,大概就露出十厘米的空隙,我把脸贴紧门缝,斜着眼睛看上堂,这次终于可以看到上堂的房子了。但上堂房间的门却关着,只可以偶尔听到钟大那战栗的声音:“来啊,我怕你啊?”
紧接着,房间里传来了撞击的声音,也有铁类工具的打斗声,似乎房间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打斗,可是事后确认,此时的房间里只有钟大一人。在钟大不断地咆哮、呐喊、自语之后,他的声音逐渐变得嘶哑,声音持续了三分钟左右,然后就平静如初了。
正在我胡思乱想,担心钟大会发生什么事之时,突然,上堂的门被打开了,紧接着,闪出一个人影。在门缝中窥视的我吓了个半死,妈呀,我见到了一个衣衫褴褛、污浊不堪的家伙,难道是鬼?这家伙拿着一把大斧头,拖着疲惫的步伐在走廊上徘徊,然后在屋檐下蹲了下来。此时的我发现自己的腿有点软,动弹不得。那家伙不会发现我在注视着他吧?他拿着斧头,不会是要来砍我吧?我的心跳加速,大脑一片空白。
我不敢再向外面望,轻轻地把门掩上背靠着门,心中念着:“五显华光大帝,要大显威灵,保护你的炉下弟子平安无事呀!”然而,可喜的是,我似乎听到了钟大那熟悉的声音:“来呀,来呀,我砍死你。”尽管声音有点微弱,但我敢肯定是他。接着,我听到了磨斧头的声音,这下我倒是有点放心了,因为在上堂的屋檐下,有个磨刀石,他们几个山工经常在门口磨刀的,不是人怎么会磨刀?只是在这个时刻,磨刀发出的声音还是让人毛骨悚然。
过了一会儿,磨刀的声音消失了,估计钟大也回房间了,之后房间里再也没有传出钟大的声音。再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听到了热闹的声音,估计是其他三个江西老表回来了。但这让我非常纳闷,当他们回来后,钟大的那副模样正常吗?如果不正常,这三人怎么会毫无反应呢?好像一切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当天晚上,我睡得不踏实,在恍惚中我也梦到了一个身穿黑色棉袄、头戴黑色毡帽的老人。第二天,我把我昨晚的所见所闻告诉了爸妈。我妈听后,说道:“这就奇怪了,难道烧点钱给他都没有效果?没有理由呀!”
“什么烧钱?”我大惑不解地望着我妈。
我妈叹了口气说道:“看来又是七叔公搞的鬼!”
我惊讶地嚷道:“啊,七叔公?”七叔公就是邻居南叔的爸爸,上堂房子的业主。又是他搞鬼?难道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
此时,爸妈的神色都很凝重,眉头紧皱。我担心地问妈妈:“七叔公不会阴魂不散吧?”
“应该不会。”我妈一本正经地说,“他死时都已经81岁了,按农村人的说法,60岁都算‘上寿’,有几个人能活到81岁?他可谓儿孙满堂,幸福过世呀,怎么还会阴魂不散呢?一般阴魂不散的人,即使存在,也是因为在阳间有什么怨气没有发泄,才会来作怪啊。”
不过在我妈跟我爸的交谈中,我得知,钟大所见或所梦的这个人肯定是七叔公,因为七叔公生前的平常装扮就是身穿黑色长棉袄,头戴黑色毡帽。七叔公生前,我只是四五岁的小孩,不过,对他还是有一点印象的。钟大是个异乡人,之前也从来没有听说或者见过已经死了多年的七叔公。那他随便描述一下老者,也不会如此巧合地描述成七叔公吧,这不会是巧合,毕竟他现在所住的房子就是七叔公的。
而我妈口中的“又是”,表示曾经发生过什么。没错,是曾经发生过,那是我爸的亲身经历。我妈接着告诉了我一些不知道的事。
大概是我读小学的时候,我爸有一段时间独自睡在上堂的房间。农村人嘛,早起的鸟儿才有虫吃,干农活要起得特别早,比如挑水、浇菜什么的,所以我爸平常都是早起。但有一天早上,我妈去上堂房间拿些农活工具,一打开房门,发现我爸平躺在地板上面。原以为我爸早已经去田间干农活,没想到他竟然一个人睡在冰冷的地板上,我妈吓了一大跳,立即摇醒了我爸。但我爸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说了一句话:“七叔不让我睡在他家的床上,所以把我抬到了地板上睡觉。”
见鬼了!我妈立即扇了我爸几巴掌,然后扶起了他,逃离上堂房间,冲了白糖水给我爸喝。之后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爸那天晚上冻坏了(毕竟是冷冰冰的地板啊),结果他大病一场。我妈因为这件事而大做法事,烧香念咒,大烧冥钱,叫七叔公在天国好好“生活”,之后果然平安无事。
现在,江西老表的到来,让这位归西多年的七叔公再来作怪,实在让人胆战心惊。我问我妈,现在江西人睡的这张床是否就是七叔公睡过的,会不会是床的问题呢?我妈说,现在上堂房子一楼的床还是以前的那张,而棚上,是没有床的,因为棚本来就是木板搭的,所以江西人中的两父子直接睡在棚上,而钟大两兄弟直接睡在这一楼的床上。
一般情况,农村人的老者去世,会在老人尸体安葬(当时还是土葬)之后,把老人生前的衣服、盖的被子、睡的床统统烧掉。而我记得,七叔公不是在上堂的屋子里去世的,而是在外围房子的另外一间里去世的,这就意味着,上堂屋子的床不是七叔公生前睡的床,而是南叔夫妻俩睡的。
虽说那不是七叔公睡的床,但上堂的房子毕竟是七叔公曾经的家,因为之前开伙做饭就是在上堂,因此他说那是他的家,那是他的床,应该是毫不过分的。过分的是,他说这话时,不是在生前说的,而是在死后说的!
这让人搞不懂。不能再这样冒险了,我建议我妈立即叫钟大搬走。我妈也觉得有道理,于是跟我一起来到上堂,叫钟大出来。我妈开门见山地说道:“钟大,你们在这里住,我担心你们的安危,你们还是搬走吧,下寨的几户人家都有空房子,要不你们搬到那里去?”
钟大笑了笑,挥挥手道:“不用搬了,这里住就挺好的。”
我妈着急起来,道:“我听江儿说,你上次给‘人’掐了,晚上又跟老人打架什么的,这样下去不行呀,还是搬走吧。”
钟大道:“呵呵,确实是有问题,不过没关系,我有办法对付的,你们别担心。”
我妈无可奈何,只好作罢。唯一的一次谈判无效,灾难最终无法避免!
在灾难到来之前,钟大在一次跟我的闲聊中说,那个老者七叔公又来找他了,他真的拿起斧头向黑暗的半空中舞动了几下,七叔公就消失了。只是这一次的情况不同,他舞动斧头之后,听到了一阵哭声—竟然是一个孩子的哭声,然后见到了这个老者,牵着这个小孩子如风似雾地飘走了。
我不相信钟大,因为我感觉他越说越离谱。然而,当我爸妈听到这话之后却大吃一惊。
他们私底下对我说:“钟大说得一点不假,是有这么个小孩,6岁时就夭折了,当时病死在上堂的屋子里,他是南叔的儿子,即七叔公的孙子。”毋庸置疑,这次钟大又猜对了,这也太他妈的诡异了吧,钟大似乎有阴阳眼,可以看到这么多事情。跟他一起住的钟二和两父子,难道可以忍受钟大的这种异常吗?对此,我的想法是,钟大对自己遇到的事情,视作做梦,不会因此而神经兮兮的,其他三人也就没有太留意。
但当三人留意到这一点时,悲剧却已经铸成。
据说那是周三晚上,有点阴雨,让人备感压抑。整个寨子里的人都已经睡了,除了鬼魂,估计没有什么东西会在外面游荡,夜,寂静得可怕。子夜,突然传来了凄厉的惨叫:“救命啊,救命啊!”
当时很多人都惊醒了,大家明白救命声是从上堂的屋子里传出来的,因为救命声很独特,是用普通话喊出来的。当部分村民匆匆忙忙跑到上堂屋子时,看到钟二在房间的角落里拼命地抱着他的哥哥钟大,看来是不让钟大挣扎,而此时的钟大脸色苍白,头发蓬乱,看起来像刚刚经历过一场厮杀。房间内的东西杂乱无章,凳子、椅子横七竖八地斜靠在墙边。细心者发现地板上留下了一大摊血,而这些血是从棚上沿着楼梯流下来的!
没错,从棚上传下来的哭声证明,应该是两父子中的一人受伤了。有热心的村民,当然包括我爸妈,走上楼梯,才发现,受伤的是那位中老年人。他应该是大腿受伤了,其儿子用几件衣服帮他包扎了伤口,这几件衣服早被血染透,旁边还放着几件因擦拭而沾满血迹的衣服,这位中老年人看起来几乎虚脱。大家都被这情景惊呆了,还是一位有点医学知识的“赤脚医生”先反应过来,说大出血,一定要先止血,应立即送镇卫生院。
担架就地取材—竹梯上面铺上棉被。把受伤者抱上担架时,有人看到了这一幕,差点吐了。据说中老年人的那条腿似乎断了,因为腿好像分开了一样,虽然经过了包扎,但仍然像藕断丝连的样子。其实即使腿断了也不奇怪,因为作案工具就是那把锋利无比的斧头,这把斧头是砍树用的,如果在人毫无防备之下,一斧头砍过来,并且是砍到大腿,不断才怪呢。
大家估计,中老年人没被抬出村口,就可能断了气,但他的儿子恳求大家帮他把其父抬去医院抢救。大家飞一般地走了一个半小时的山路。抬到镇卫生院,医生大摇其头,不接受病人,不愿意治疗。
死人了!钟大就是罪魁祸首,他就是故意杀人犯。但看他神志不清、满脸惊恐的样子,谁能相信他有胆量砍自己老乡一斧呢?就当做钟大有间歇性精神病史而导致了这件事情吧!但为什么他的叙述中话里有话呢?据说在清醒之后,他说他就是要砍那个老者,而自己不知不觉地走上了楼梯,然后对着老者来了一斧,但有人相信吗?其他人不知道相不相信,至少钟二相信他:第一,钟大没有精神病史;第二,在棚上睡觉的那对父子是钟大的岳父和小舅子,试问,谁会砍自己的岳父一斧啊!
无奈,人死不能复生,村长倡议拿点“香油钱”给他们,村民都慷慨解囊,同时,猜测着为何七叔公要如此残害良民,难道就仅仅因为生人占用了他的房子吗?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钟大清醒之后,无数次哭得死去活来!可是,小舅子在痛定思痛之后,反而安慰道:“姐夫,节哀,人死不能复生。”小舅子的言语,让人觉得话里有话,可是,在众人面前,他始终缄口不语。后来江西人搬走后,家人收拾棚上的东西时,发现南叔留下的箱子竟然被撬开了。
一年之后,南叔回老家探亲时,听说此事,感慨万千。他那个箱子里面装的只是那个夭折孩子的脐带,用布包了起来,当时作为爷爷的七叔公对孙子的夭折非常伤心,所以一直把脐带保存在箱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