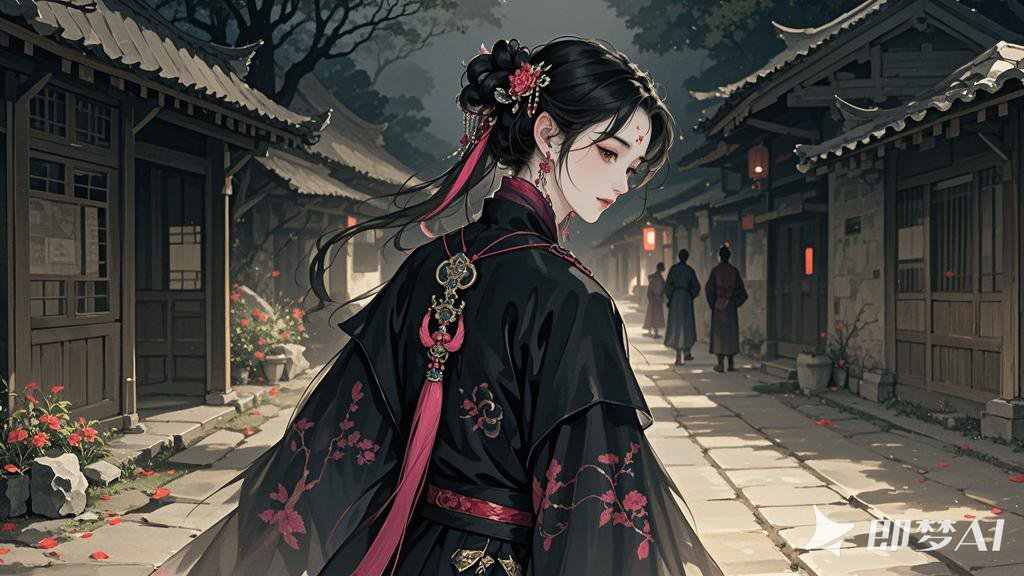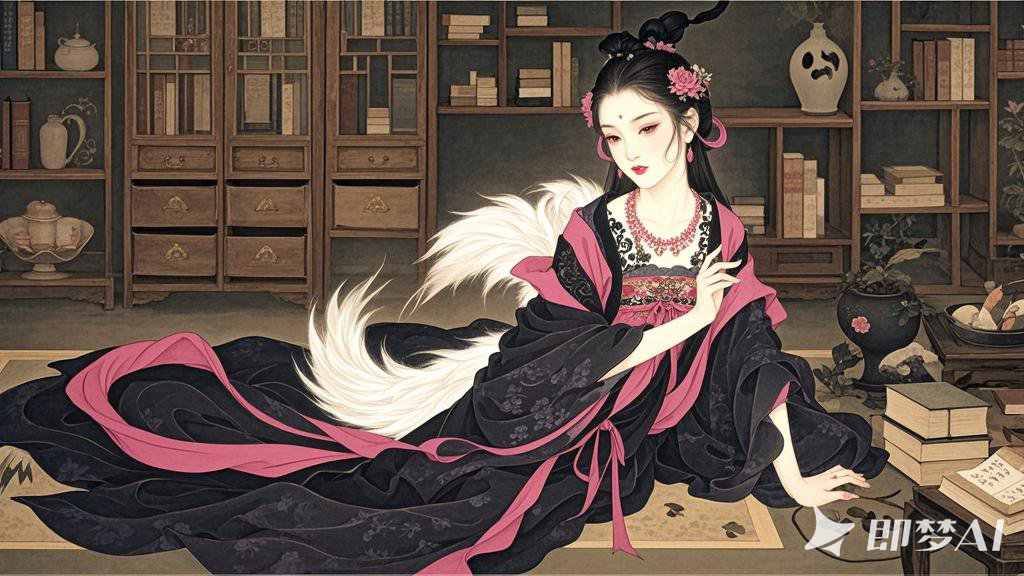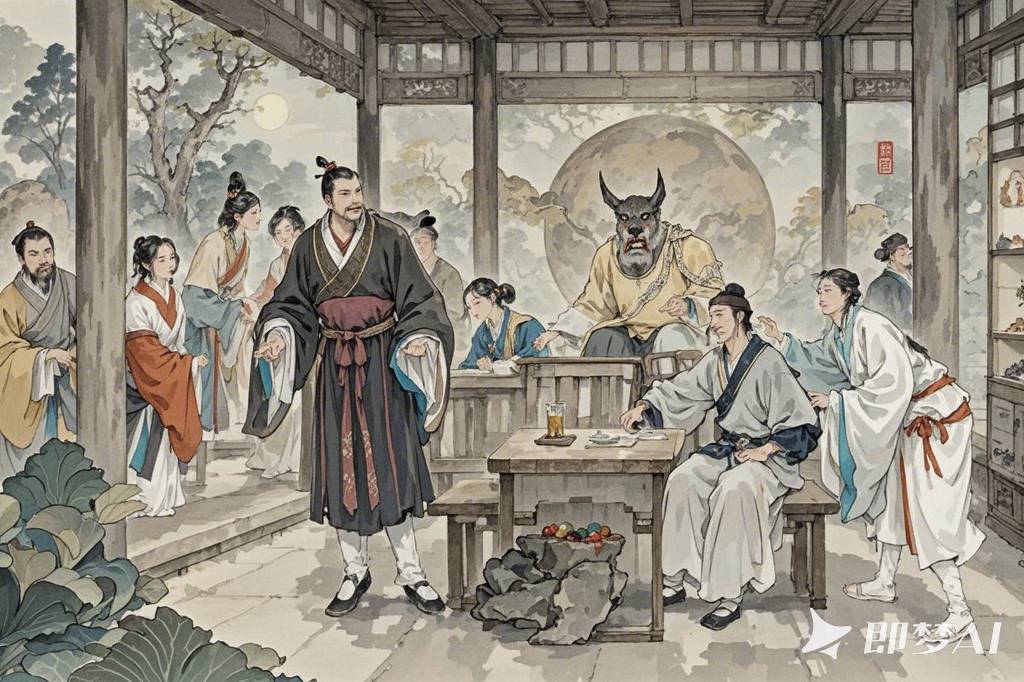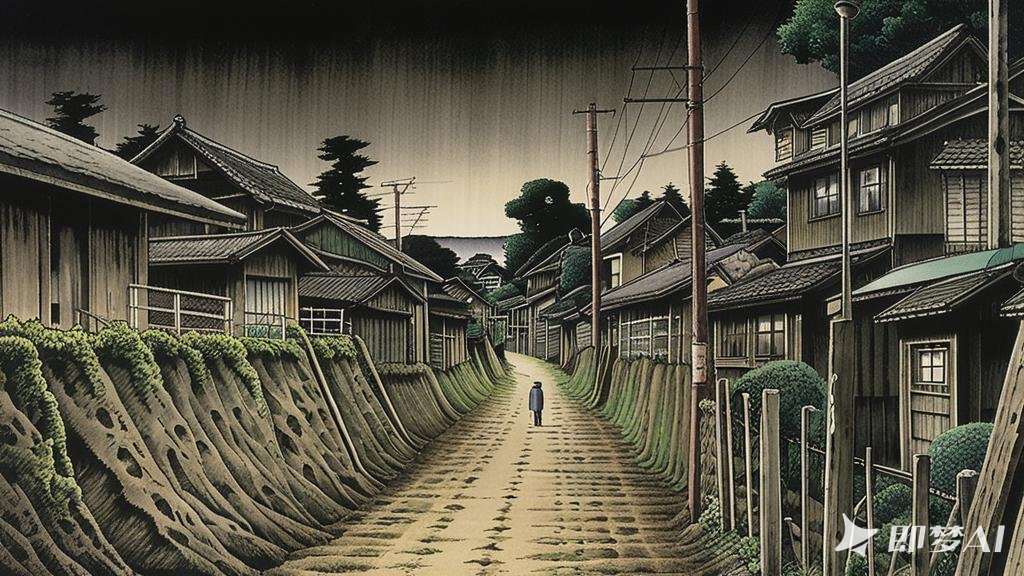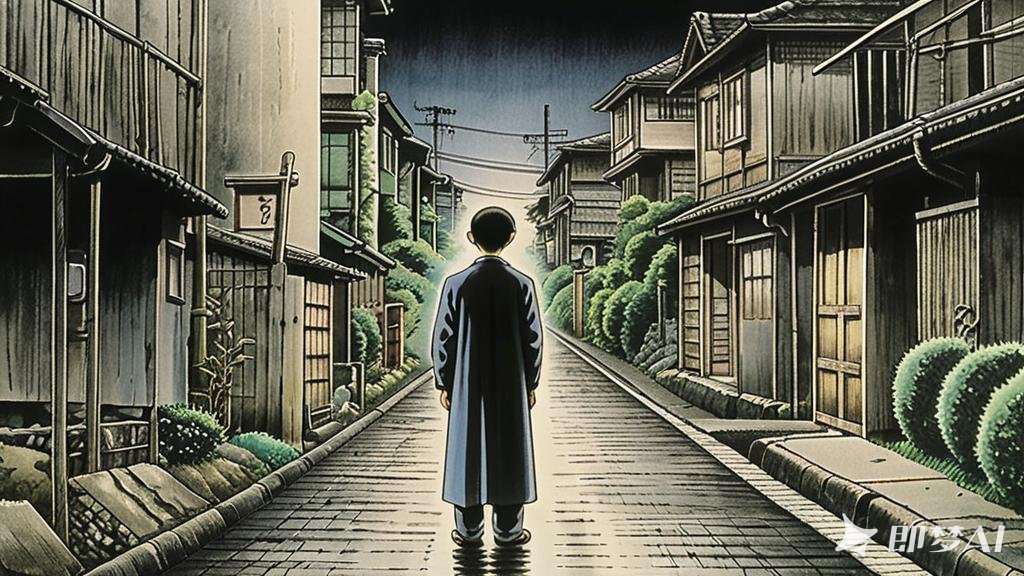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七、八、九三个月,是明朝建国以来气氛最阴森的三个月。七月中旬,当了四十八年皇帝的朱翊钧驾崩。朝野之间,抑欢禁乐,人人强作愁颜,来为大行皇帝举哀。紫禁城里孝幔低垂,香烟袅袅,一派惨淡景象。依明朝旧例,皇帝殡天后,皇太子朱常洛已于八月初一即了皇位。但万历的凶事尚未操办完毕,新登基的皇帝却又忽然病倒了,而且病势来得猛烈。太医院几位医术高明的御医共同会脉后,连拟了四副重药都没有扭转病情。皇帝气得大骂太医无用,而太医院院使亲自进宫去把脉,也没敢说出病因,只开了不少补元气的药物,皇帝吃了毫不见起色。到了八月十六日,宫内传出新闻,说皇帝已经起不来床了。
新君刚刚即位半个月就不能再理朝政了,这可急坏了内阁的几位阁臣,由于天天由六部及各省督、抚呈上的奏折不下数百件,其中有不少是急待办理的,皇帝病倒,不能进行朱批,只好压着不办。内阁首辅方从哲开始时倒还沉得住气,但几天以后也感到坐不住了。方从哲是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资格入阁的,他在万历朝担任了七年首辅,很能处理君臣间的关系。万历皇帝三十多年不和群臣晤面,但方从哲替万历草诏的各项谕旨,几乎没有受到过驳斥,那是因为方从哲设法交结了万历最宠爱的妃子郑贵妃的缘故。万历驾崩后,方从哲扶持皇太子朱常洛登墓,原以为新君正值四十多岁的盛年,会励精图治。亲自披览公文,省却本身不少麻烦。没想到这位新皇帝连万历都不如,万历虽然不理朝政,但总还能在草诏的圣谕上作作朱批,而这位新皇帝病倒后连朱批的能力也没有了。圣旨无法下发,国事无法摒挡。而六部九卿催促批复的奏折几乎每天摆满一桌子。最近连阁臣们也在背地里埋怨首辅办事不力了,怎不令他心急如焚?
今天:方从哲刚一来到朝房,内廷就送来了一道紧急公函。打开一看。原来是皇帝有病乱投医,昨天竟擅自斥退了太医院医官,而请内侍崔文升给他看病。崔文升开了一个方子,皇帝吃后大泻不止,一夜之间起厕三四十次,现已晕厥不醒,急请内阁处置。方从哲看罢,心中又惊又气。惊得是万岁病危,社稷难以安定,气得是内府二十四衙门,那么多官吏,竟不能劝阻皇帝,而让一个不懂医道的内侍乱用虎狼药。他一壁急传太医院御医进宫抢救,一壁关照内阁阁臣赶到太和门前等候宣召——他估计皇帝假如病危了,肯定会宣召阁臣布置后事的。
当方从哲带着阁臣们赶到太和门时,内廷已经乱成了一团,皇帝晕厥不醒,太医们一筹莫展,几次派人进宫催问抢救情况,始终未见回旨、而从太和门里赓续传出的紊乱脚步声,说明情况危机。方从哲心中十分严重,急切地等着太医的诊断效果。
天近午时了,几位御医才从宫中出来。因为首辅有话,要及时禀报万岁的病情,所以领班的御医专程来朝房探求方从哲。这位御医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平日与方从哲交往很深。所以说活毫不忌讳,刚—晤面就压低了声音说:“上头的病不妙。”方从哲有些迷惑地说:“刚刚四十出头,怎会病成这个样子。”老太医摇了摇头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皇上精损过重,常言道‘寿命之本,积精自刚’,所以太医们一贯使用固精建中之类的药物,为的是渐复其真阴之不足。这类药物本是慢工,岂能仙人一把抓?皇上埋怨服之无效,而滥用泻药,以致我们数月凋治之功毁于一旦。”方从哲从老太医的埋怨中已经感到不妙,不觉脱口问道:“莫非不好办了?”老太医叹了口气说:“假如不再乱用庸医,只以充血生精之药调理,照旧有望的,只怕……”方从哲赶快接过来说:“我当进宫劝谏,请皇上按太医院的医案凋养。”老太医拱拱手说:“多蒙大人相信。”说罢匆匆离别回太医院去了。
送走老太医,已经过了中午,方从哲匆匆用了一点午餐,正预备写劝谏皇帝信赖太医院的札子,却听到太和门里一叠声的传呼,“皇帝急召首辅入宫。”从这道传唤看,皇帝确实是病危了,方从哲定了走神,待情绪稳固下来后,才随着前来引路的太监向后宫走去。
进了乾清门,后宫的气氛使人感到克制。万历皇帝的凶事还没办完,后宫各院的门前还悬挂着长长的孝幔,盛炎天气,各殿宇的大门却都紧闭着。偌大一座宫院中,除了偶尔有一两名太监匆匆走过外,阗无人声。因为天热,宫院中那些名贵的花树,也都垂着叶子,彷佛在想什么心事。
朱常洛的寝宫在乾清宫西南的养心殿,此时殿门紧闭,还垂着一张大竹帘子,所以一进殿就给人一种黑暗的感觉。方从哲扫视了一下殿内,没有发现一个宫娥内侍,只看见殿中间龙案上,燃着几根龙涎香,一缕香气扑鼻而来,因而屋里的空气倒不显得浑浊。引路太监轻轻走到西暖阁前,撩起了低垂的竹帘,只听新皇帝用薄弱的声音传旨:“请方老师进来!”方从哲不敢怠慢,整了整衣冠,面色端庄地走进暖阁,双膝跪倒,恭敬地说:“臣方从哲见驾吾皇万岁!”“起来,赐坐!”早有一名内侍搬过一只雕龙硬木圆凳来,请方从哲坐下。方从哲这才低垂着头,用眼睛的余光偷觑了朱常洛一眼,只见他面色苍白,三络长髯虽在病中,却梳理得十分划一,头上缠着一块沾湿了的黄绫子,显然是为了降温。从这统统迹象看,皇帝的病虽重,却不象有致命的伤害。朱常洛伸出有些颤抖的手握住方从哲,说:“朕这几日头子眩晕,身体软弱,不能临朝,统统大事都烦老师操劳了。”方从哲赶快接道:“万岁天恩浩荡,从哲敢不竭尽全力报效国家?”朱常洛说:“朝中政事老师可代朕朱批,太子生性懦弱,也望老师扶持,后宫妻妾……”说到这里他感到气力不支,喘息了好一阵才接下去:“尚将来得及册封,老师可仍旧例拟定名份。”这几句话无异是交待后事了,方从哲恭敬地凝听后安慰说:“万岁春秋正富,偶染小疾,原无大碍,望安心调养,万万不要误信蜚语,作践龙体。”朱常洛摇了摇头忽然问道:“寿宫可曾统统?”这一问使方从哲感到十分为难,他不知道皇上问的是已经驾崩的万历的寿宫照旧他本身的寿宫,临时不好回答,思索了一阵才说:“万岁放心,大行皇帝已安葬完毕,天寿山地宫于前天开始复土……”,没等他说完,朱常洛已经不耐烦了,打断说:“朕问的是朕之寿宫。”方从哲慌忙跪倒在地颤声劝道:“太医院御医已禀报过,万岁目前不过是体质衰弱而已,哪里便有天崩地坼的事?”朱常洛讨厌地说:“太医院一帮庸医,朕信不过。”“万岁若信不过太医院,臣当传檄天下,广召名医。”听到广召名医几个字,朱常洛蓦地想起一小我来,就问:“听说鸿胪寺有官员来进药,现在为何还不送来?”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曾上本说他有仙方可治万岁病症,但臣与内阁诸臣计议,以为不可轻信,所以已将李可灼斥退了。”朱常洛面露嗔色,沉默了一阵才说:“太医无用,仙方又不可信,难道叫朕束手待毙?”方从哲吓得连连叩首说:“微臣怎敢?只是李可灼之言实不可信,皇上三思。”朱常洛挥了一动手说:“纵不能医病,也断不会要命吧?你传旨下去,朕要试试这个仙方。”方从哲知道,从万历的爷爷嘉靖皇帝起,就信仰道教,求炼长生不老的仙丹,这股风气由来已久,万历暮年几乎每天都要坐在丹房里与那些老道们一路炼丹,看来新皇帝也深谙此律,迷信“仙方”,这是难以劝阻的。只好推诿道:“待臣与六部九卿商议后,再来禀明皇上。”朱常洛说话太多了,感到底气不足,挥了挥手,示意方从哲不要再说。方从哲赶忙与几名宫娥伏侍皇帝躺好,看着他闭上眼睛,微微喘息,才磕了一个头匆匆退了出来。
接连三天,后宫里赓续来人催问:“李可灼的仙丹是否送来了。”方从哲只是推拖,到了第三天下战书,皇帝的亲随太监来到体仁阁,说皇上降旨,着李可灼速带仙丹进宫。方从哲无奈,只得与阁臣韩议定,由他二人陪同鸿胪寺丞李可灼带所进之药进宫见机行事。
鸿胪寺丞李可灼是个五十开外的老人,他面形清癯,举止萧洒,确有点道骨仙风。所进的“仙丹”盛在一个十分古朴的锦匣内,方从哲打开锦厘,立即飘出一股沁人心肺的清香,使人感到五内愉快。再看那仙丹,却是一粒红得如同玛瑙般的药丸,光泽晶莹,灼灼醒目,确实不像凡间所有,据李可灼讲:此仙方乃是他年轻时节在峨媚山采药时得遇一位仙长所赠,所用药料均采自神府瑶池,非人间所能得到,能治百病。这么一说连方队哲也不能不信了,急忙带着李可灼来到了养心殿。
朱常洛显得比前几天更削瘦了,体质衰弱,竟连侧身半坐也觉困难,只好平躺在龙床上。但他的神智十分清楚,见方从哲与韩进来,劈头就问:“仙丹可曾带来?”方从哲跪着奏道:“李可灼已携仙药进宫,只究竟能否治病,臣尚不敢妄语,请皇上明断。”这时,李可灼也捧着“仙丹”跪在了韩的后面。朱常洛示意把药呈上来,方从哲赶快回身取过药匣,匍匐到龙床前双手把药递了上去。一名贴身宫娥接过药匣缓缓打开,马上全屋都迷漫起淡淡的清香。李可灼见四周大臣疑虑神色,先自服一丸。大臣方才放心。而朱常洛一见仙药红润晶莹,就觉得不同凡响,况且此刻药物的清香又使他顿觉愉快,于是命人取水来,急匆匆地把药吞下去了,整个西暖阁内从宫娥内侍到方从哲、韩都严重地等着皇帝的反映,只有李可灼好像胸中有数,脸上呈现出一副自傲的神色。皇帝服下药去,就闭上了双眼,有一刻多种—动也不动。守卫在两侧的臣子们有点沉不住气了,方从哲用眼色示意传事太监看住李可灼,勿令逃脱。就在这时,皇帝却展开了双眼,呼唤宫娥携扶,想坐起来。方从哲刚要阻拦,朱常洛已经坐了起来,彷佛一会儿健康了很多,脸上露出了笑颜,连夸:“果然是仙药,仙药!”又赞美道:“李可灼是个大忠臣。”皇上的这番行为使方从哲、韩不能不信赖仙药的灵验了,二人齐声问:“万岁此刻感觉如何?”朱常洛说:“朕只觉遍体清凉,似再无衰弱之感。”说罢探出身来叫道:“李可灼!”李可灼伏地轻应:“微臣在。”朱常洛说:“朕服仙丹果然见效,请你明天再进一丸来,也许就可痊愈了。”李可灼答道:“臣家中尚有一丸仙丹,但仙长曾辅导过,需在第一丸后三天再进第二丸,臣当于三天后再献灵药。”朱常洛说:“联病好后,肯定给你加官进爵。”李可灼磕着头说:“微臣不求加官进爵,只愿万岁龙体得康复真元,就得偿所愿了。”朱常洛更是赓续地颔首赞美“忠臣,忠臣。”方从哲跪着扶住皇帝说:“万岁刚刚复康,还望息心调养。”朱常洛点颔首说:“朕知道,你们跪安吧!”方从哲恭恭敬敬地站起来,带着二位外臣退出了养心殿。
夏历八月末,是北京的金秋季节,在养心殿的宫院里,有几盆硕大的桂花正在盛开,金黄色的花朵簇簇团团,馥郁的暗香弥漫天井。大殿里,那紧闭了十几天的殿门已被敞开,任阵阵花香随风飘入西暖阁。朱常洛坐在龙案前,心境很是欢快。自吃了李可灼的“仙丹”后,不知为什么,疾病宛如彷佛一会儿被驱走了一半。两天来,他除了时常坐在龙案前养神外,居然还有两次走出了殿门。看到那生意盎然的桂树,他感叹因为有病竟然没顾上浏览中秋的月色。想想今天就是八月三十日了,李可灼的第二粒仙丹将要送来,内心更是喜悦。
朱常洛和他父亲万历皇帝一样,十分迷信所谓的灵丹妙药,这次吃了“仙丹”,病势陡然减轻,更使他对仙丹百般敬服。他清楚地记得十八年前,父皇万历也曾得过一场大病,当时已认为没有恢复的余地了,于是传了遗诏,把太子后妃托孤给首辅沈一向。但一夜之间,病情忽然大愈,据说就是吃了仙丹的效果。想到这里,他更盼望快点得到第二粒仙丹,所以从上午他已派了六拨儿太监去催促方从哲,叫他火速传李可灼进宫。但如今天气已近申时,李可灼还没到来,他不觉有点焦躁了,嘴里赓续地叼念着“首辅误事”。直到申末时刻,太监才报道方大人、韩大人陪着李可灼在宫门前候旨,朱常洛迫不及待地说:“传!”
力从哲今天可为了大难了。三天前在皇上的催逼下,他引李可灼进宫献药,虽然当时就收到了结果,但凭他多年的阅历,总觉得这好像是生理作用所致,并不肯定是药的神效。回到府中后,就有几位心腹幕僚前来探问情况,他们与方从哲的看法同等,都劝方从哲不要再引李可灼进宫。尤其是太医院的几位太医,众口一词地否定“仙丹”的作用,他们透露表现,假如首辅再引入送什么“仙丹”,他们就集体上辞呈了。第二天又有几名给事中上疏,弹劾方从哲以首辅之尊,不能停止内侍乱用虎狼药,又滥引荒诞之人进宫献荒诞之药,弄得方从哲有口难辩,所以他预备再次斥退李可灼。但从后宫传来的新闻却是皇上已能下行走,这又使他对仙药依靠着一线昏黄的盼望。他也曾寻访了太医院院使,院使告诉他皇帝的复康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太医院迩来所献的医方起了结果,一种竟可能是病入膏盲的“回光返照”,无论怎么说也与仙药不干系。这使方从哲一,时难以断定孰是孰非。今天一早,皇帝就派人催仙药,方从哲是一压再压,企图耽搁,但中午以后,皇帝催促更紧,并发下圣谕,假如内阁阻拦进药,就以抗旨欺君论处。他才无可奈何地将李可灼召到内阁,再四叮问,李可灼力保仙丹有神效,方从哲这才拉上韩一同陪李可灼进宫。
进得宫来,见皇帝居然隐坐在龙案前,神气确比前天好多了。方从哲总算略微扎实了一点,内心又有点信赖仙药确有奇能了。今天进来的这粒红丸,比前次的略大一点,色泽也更加光艳。朱常洛接过来后,细心端祥了好一阵,脸上露出了一种难言的高兴。宫女捧上淡人参汤,朱常洛很快地就着参汤把药服下了。李可灼看皇帝服罢药,跪请他上床歇息,朱常洛却不在乎地摆了摆手说:“用不着,朕今天精神很好,李爱卿献药有功,来日定当封赏,”说罢,起身在地上踱了几步方步,又笑着对方从哲说:“方老师,你看朕明天是否可以临朝了?”方从哲娓婉地劝道:“万岁且再将养几日,待龙体大康后再临朝不迟。”朱常洛颔首答应。为了不再使皇上过分劳累,司礼监随堂太监及时地截断了他们的发言,把三位外臣直送到隆宗门才挥手言别。
九月初一,是新君登基一个月的喜庆日子。内廷诸司见皇帝病势恢复得很快,决定连夜撤掉祭奠大行皇帝的孝幔。挂灯悬彩,庆贺新君亲政。所以紫禁城里八月三十日是一夜未眠,二十四衙门连夜布置装饰宫院的运动。御用监和司设监更是忙碌,把大量红绸、宫灯送到三宫六院。各院太监们往返奔走,挂灯的挂灯,送锦衣的送锦衣,生怕明天寅时二十四衙门总管太监检查时,挑出大毛病。忙碌到后午夜,乾清宫前忽然出了乱子,只见四名年青力壮的太监飞跑着往各宫传旨,着马上停上张灯结彩,紧接着司礼监掌印太监传谕速召太医院院使率诸太医进宫,不一下子又传皇帝口谕,着乾清宫李选侍率皇太子及各宫妃嫔到乾清宫听旨,与此同时,宣召内阁辅臣、六部九卿掌院官吏进宫……这连续串的召人,说明皇帝已经病危了。等到方从哲率领着各部尚书来到乾清宫前时,太医们已经垂头丧气地从殿内走出来,乾清官里六宫女眷‘们哭作一团一皇帝在九月初一丑时二刻殡天了。
原本已经复康了的皇帝,服了一粒并非御医进呈的红丸,在夜里蓦地死去,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方从哲此刻更为严重,他已预料到明天清晨就会有无数指劾他的奏本飞进来,弄不好很可能被扣上一顶“弑君”的帽子。所以虽然他外观上还保持着平静,但心中却在暗暗地思索着为本身解脱的对策。按明朝的旧例,皇帝驾崩,他的遗诏需由内阁首辅代拟,方从哲想来想去,觉得只有行使拟遗诏的机会,申明服用红丸是皇帝本身的意见,把责任一股脑推到大行皇帝身上才算上策。主意已定,他的神情也安定了下来,以宰相的风度调理后事,居然使统统井井有条,当夜就安排好了举哀的悉数程序。
果不出方从哲所料,皇帝的暴卒引起了整个朝廷的细致。要追查皇帝死因的奏折两天之内就达数百件。其中有的奏本已经公开指出,给皇帝服泻药的内侍崔文升,最初曾在郑贵妃属下任职,后来才由郑贵妃转荐给朱常洛。崔文升竟敢用泻药摧残先皇,其背后必有人教唆。这使方从哲感到吃惊,由于他晓畅本身与郑贵妃也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假如有人说红丸是由本身引进的,再把它和崔文升联在一路,很天然地会形成一个育计划的弑君诡计。朝议一路来就很难平息,本身将成为众矢之的。虽然对这些他已有预料,但绝没有想到,事态会发展得这么快。好在他在皇帝殡天那天起就已想好了对策,他满有把握地认为,群臣如今纷纷上本,是因为不了解原形。现在只要把皇帝的遗诏发下去,群情自可平息。于是方从哲迫不及待地征得了阁臣的赞成,颁布了由他亲笔起草的遗诏。遗诏中以大行皇帝的口吻百般夸奖李可灼,并诏赐银币。方从哲以为这对堵住各言官的嘴可能会起极大作用。但他绝不会想到本身走了一招最愚笨的棋。遗诏一下,群情鼎沸,朝臣们都知道遗诏出自首辅之手,无形更把方从哲与进红丸紧密地联在一路了。大家把遗诏当成了方从哲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很多言官开门见山地把方从哲也列入弑君的行列,请求惩办崔文升,李可灼,并严查幕后主使的声浪愈演愈烈,到这个田地,方从哲也感到有点抵挡不住了。
在天启初年的内阁中,辅臣韩算是威望最高的了。“红丸案”发生以后,尽管群臣纷纷上疏追问,韩却始终一声不响。这令方从哲十分恼火。十月四日,在内阁里议处政事,方从哲问韩:“李可灼进红丸从始至终你都清楚,为什么不出来说上两句公道话?”谁知韩只是微微一笑,根本没有回答。方从哲真不知这位辅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其实韩一向在谛视着群臣的动态,他对方从哲的无过受责也寄予很大怜悯,但是他看题目要比方从哲远得多。依他的主意,对群臣要求查清红丸案、追惩幕后人的奏折,本就应采取听之任之不加可否的态度,如许很可能喊一阵就天然的息声敛气了。方从哲过早地跳出来,又是颁遗诏,又是命人申辩,现实上是本身给本身套锁链。现在方从哲成了众矢之的,而本身也是陪同进药的阁臣之一,群臣攻击方从哲,未必对本身就没有猜疑,假如在这个节骨眼—上站出来为方从哲辩护,其终局将会和他一样陷入被动局面,那么要澄清此案就比登天还难了。韩的这番苦心,方从哲怎么会知道呢?
十月中旬,追查“红丸案”的呼声达到了最高潮,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上了两道令人瞩目的奏疏,孙慎行指出:“从哲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邹元标则厉声切责:“首辅方从哲不伸讨贼之义,反行赏奸之典,即谓其无心,何以自解于世。”这孙慎行和邹元标都是朝巾最孚众望的大臣,素以忠正耿介着称。尤其是邹元标,昔时曾因反对权倾临时的首辅张居正受过很重的杖刑,被时人誉为“五直臣”之一,声震朝野。他们的奏折给追查“红丸案”首恶定丁基调,方从哲纵有一万张嘴也难以辩驳了。捧着这两道奏本,方从哲双手赓续颤抖,他回顾这几天为平息众怒所做的努力,感到本身并没有走错棋,比如在会见群臣时,他曾严明地指出:“崔文升、李可灼进药,均系先皇所请,如说内中有诡计,首先要使先帝蒙受一个不得寿终的名声,凡属臣了,于心何忍?”这本是一个义正词严的回击,足以使那些气势汹汹的言官望而生畏。谁知这个回击非但没有见效,反而如同推波助澜,使追查的声势形成了一股狂流。先前弹劾他的还只是些言官,如今连不少大臣也自告奋勇了,先前的奏本还只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以隐指为主,如今干脆指名点姓地骂起来了。更有甚者,有的奏本还翻起了老账,把方从哲倚赖郑贵妃的丑事都抖露出来了,最后终于导致了孙慎行、邹元标的奏本……秋风起了,宫院中落叶满径,寒气从门缝、窗缝中钻进来,使人遍体生凉。方从哲此刻连内心都是凉的,他感到再也无力招架这些严峻的切责了,想不到居官一世处处细心,苦心钻营,竟落了个“弑君”的罪名。事到现在要想保全身家性命,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上疏请求归隐。方从哲思来想去,终于选定了这个退身之计。他写了一道很长的奏本,一壁细心为本身辩解,一壁十分诚恳地提出了退隐的要求。
方从哲奏本递上去不到十天,天启皇帝的批准谕旨就下来了。十一月初,这位在朝八年之久的老臣,在冷落的秋风中,凄然地脱离了京城。卢沟桥的长亭前,芦荻萧萧,夕照斜映,断鸿声声,一派肃杀景象。方从哲举起酒杯,对前来送行的几位幕僚发泄了一番感叹。一阵寒风卷来,他那花白的胡须在风中飘洒,越显凄然,以至送行的幕僚都落下了伤心的眼泪。方从哲走了,在荒草侵径的巷子上,在乱云与荒草接壤的天终点,在落叶飘零的秋风中,孤独地走着一个被从统治集团中倾轧出来的失败者,但是悲剧并没有到此结束……就在方从哲离京后不久,又一批严查红丸案内幕的奏折送到天启皇帝的案头。这位十六岁的少年皇帝一生也算是充满坎坷了,还在幼年时节,本身的生母就因被人殴打而病死,而父亲一向得不到万历皇祖的信赖,几次差点被废掉皇太子的称号。好容易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却又大病缠身,现在又忽然不明不白地死去,这使他心中积聚着一股报仇的情感。方从哲正好成了他发泄仇恨的对象。所以当方从哲乞归的奏本上来后,他一点也不依恋地准了本,而如今群臣并没有由于方从哲的被贬而制止对他的攻讦,就更使天启帝觉得方从哲逃不脱弑君的罪名了。但碍于从哲乃是三世老臣,临时不好给予过重的处置,所以天启将这些奏书都留中不发,以观动静。这天上午,天启皇帝正在群臣的奏折衷探求控告方从哲的本子,却忽视发现一个特别很是认识的字体,细心看来,却是方从哲从致仕的老家发来的。奏疏写得很恳切,疏中说:“离京后无时不注目朝廷,知道群臣还在先皇考殡天事上纠缠不休,本身年老愚笨,未能阻止庸官进药,罪不容诛。为透露表现谢罪,愿乞削去官阶,以老髦之身远流边疆,以平朝臣之怨。”看罢奏折天启又有点怜悯起这位老臣来了,就把原疏发内阁度议。他没有想到,这正是远在江南的方从哲盼望他做的。
在处理红丸案的过程中,方从哲是走一步错一步,只有这最后一道奏疏算是走对了。他上这道奏疏的目的一是以恳切的言词,严峻的自责来平息公愤,二是盼望唤起一些朝臣的怜悯,能站出来替他说上几句话。效果两个目的都达到了。群臣在议论方从哲的奏折时,已有人为他鸣不平。不久,刑部尚书黄克缵、给事中汪庆百、御史王志道等纷纷上书,要求立即刹住追查大行皇帝暴卒之谜的舆论。他们的重要理由就是假如纠缠下去,朝廷不宁,且陷先帝以非善终之地,与皇家名声也不好听。如许的理由假如从方从哲嘴里说出,就能引起众怒,而从其他官员嘴里说出,就显得有些道理。但天启认为这种辩解并没有搞清红丸案的原形,临时难以决断。这时,一向缄默无言的阁臣韩终于站出来说话了。韩以一个亲历者的资格出现,把当时他目睹的统统事实都细致地说清楚了。分外是方从哲当时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情景,被描绘得十分详细。最后,韩才提出“红丸”一案,纠缠了一年多,但真正置先皇于死地的崔文升和李可灼到如今也没有处置,这两小我虽然乱用药物,但也确实是奉旨进药,可以适当惩处,红丸一案则不宜继承深究。
韩在万历年间就是个有名的老成之臣,居官十余年处事公正,并绝不趋炎附势,很受群臣尊仰,而且他和刘一憬都是在进红丸的前几天才入阁的,与原内阁中的党派之争没有关联,入阁后又一向陪伴方从哲摒挡进红丸之事,说出的话是可信的。所以他的奏折报上后,很快地使一场风波平息了下来。不久天启皇帝圣旨颁下,“将李可灼削官流戌边疆,崔文升逐出北京,发往南京安置。”一场轩然大波,到此总算结束。但是朱常洛为什么在一夜之间蓦地暴死?李可灼所献的红丸究竟是什么东西?却一向是个谜。三百余年来,尽管史学家见仁见智,设想了种种答案,但没有一种能令人佩服,因此红丸一案成了千古之谜,而围绕着一代皇帝猝死所发生的一场宫廷政治斗争,却深刻地揭示了明朝末年上自后妃、诸王,下至宦官、外戚、阁臣、九卿、言官、外吏之间激烈的门户之争。透过它,我们终于看到封建社会晚期的种种陋政和积弊,所以直到现在还有人把发生在明末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列为理清明代政治斗争脉络的钥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