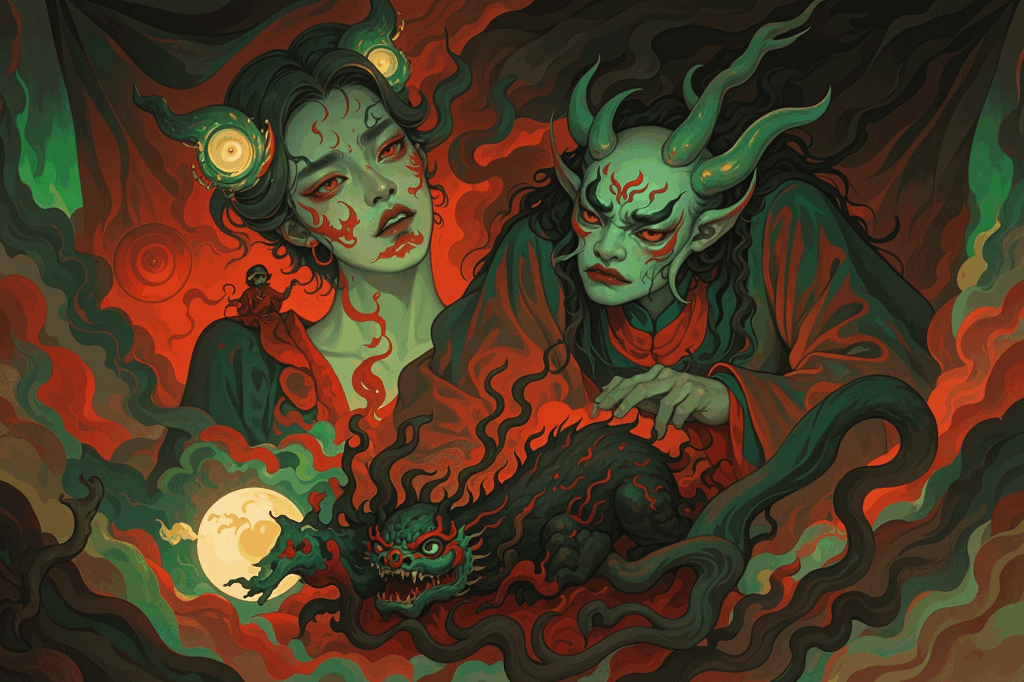在我念小学时,学校的左侧后上方有一座独立的房子;也可以说是一个独立的寨子,其寨子的主人—善婶,精打细算,亦农亦商,她充分利用了小学生嘴馋的毛病,办了一个家庭式的小卖部,物品虽然并非琳琅满目,但是小部分零食还是有的,当时我极少帮衬她的生意,但很多同学多多少少会去买点小东西。
一天中午,我的一位叫大拉的学弟,控制不住自己嘴馋的毛病,趁着下午第一节自修课还没有开始的时候,跑到小卖部买东西。让人觉得诧异的是,大拉回来时,他带回来了不少零食,羡煞旁人。据说他很大方,给班上同学每人分发一颗水果糖,对跟他要好的,还额外多分一些零食。如果是之前,他去买东西,绝对不可能一次性买这么多,这让人多少有点怀疑。果然,整个下午上课时,大拉心不在焉。下午放学后,同学们陆续离去,大拉却留了下来。他鬼鬼祟祟地扯住了另外一个小鬼头文廷,偷偷摸摸地向学校后面那个充满无限诱惑的寨子走去。
让他们郁闷的是,大老远就看到善婶和她的两个小孩正在寨子门口喂鸡,这让他们不得不中止自己的计划。可是,当他们潜伏一段时间后,刚想离开时,看到善婶带着两个小孩出去了,对此他们喜出望外。当时正值夏日,白天很长,估计善婶趁天黑之前,外出干点农活。善婶的寨子很有特色,有两个门,外面用泥砖围了起来,围墙有两米多高,围墙上还倒插着很多破碎的玻璃。从学校过去的那个门叫东门,还有个西门,通向我村的大道。西门虽然开通没有多少年,但此时略显残破。善婶和她的家人外出时,都会把东、西两门同时锁住,其安全程度可想而知,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即使家人外出,他们家中还有一个很少露面的人留守,看护家中财产。
当文廷看到善婶他们走后,他压低声音,兴奋地对大拉喊道:“大拉,善叔婆他们出去了,快点过去!”
两人心有灵犀,冒冒失失地走到了善婶家的寨子东门口,却发现大门关得好好的,应是里面用门闩闩了起来,大拉抓了个石头,敏捷地爬到大门口旁边的一棵树上,俯身用石头打掉了玻璃,然后跳到了围墙之上,纵身一跃,大拉的身影消失在围墙上。接着,大拉想去打开门闩,却发现里面已经上锁,他从门缝里对外面的文廷说:“你就别进来了,在这里把守,等下来接应我。”说完独自一人走了进去。文廷站在东门外望风!
大拉肯定经常光顾善婶的小本生意,对她的屋子结构了如指掌,叮嘱文廷后,他轻车熟路地来到善婶卖东西的那个房间门口,据说当时的走廊里一片寂静,那天傍晚确实是偷东西的好时机。他轻轻地把门一推,让他惊喜的是,门竟然没有锁。他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兴奋之情油然而生,慌忙之间,拿起一包包零食之类的东西往自己的袋子里塞,很快地,袋子里塞得满满的。据事后家长透露,大拉第一次做这种勾当,难免紧张,时不时向屋子外面张望。
黄昏下的屋子,在后山阴影的笼罩之下,显得有点阴暗,而靠近门口的一面墙壁上摆满了货架,屋子靠近里面挂着一张褐色的布帘,布帘把一间房子隔成两半,使靠近门口的货架处显得更加阴沉。正在淘货时,大拉突然感觉到布帘后边矗立着一个高大的身影!
刹那间忙碌中的大拉停了下来,怎么突然之间有人在?不是人,是鬼!大拉吓得浑身发抖、手脚无力,连包在衣服里的东西都掉了出来,正在他不知所措之时,布帘后面传来“咯咯咯”的笑声,那笑声充斥着整个空旷的房间,令人毛骨悚然。大拉赶紧把东西一扔,撒腿就跑,可是,慌乱中,他的衣服被货架挂住了,他用力一拖,货架顿时向外倾斜。伴随着货架的倒塌,货架上的东西全掉在地上。大拉也摔倒在门槛处,他不顾疼痛,扭头过来,看布帘后面的高大影子。
这时,布帘被慢慢地掀开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缓缓走了过来,脸上露出莫名其妙的微笑,打着赤脚,走路毫无声息。大拉吓得魂飞魄散,双手捂眼,大叫起来:“妈妈呀,鬼啊,我没有偷东西呀!”
可是,大拉的不打自招却毫不见效,这男人无动于衷,他一声不吭地走到大拉的旁边,伸出粗壮的手臂,抓住大拉的小手,大拉被其缓缓提起,继续号啕大哭,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男人放下了他,把他慢慢拖到布帘后面,布帘后面有一张床,床上的墙壁上贴着几张黄色的符头。男人让大拉坐在床上,大拉不敢反抗,战战兢兢地一动不动。大拉脸色铁青,哽咽着。而奇怪的是,那男人坐在床对面的一个凳子上,面对大拉,时不时地冷笑一声。他们就这样对峙着,持续了二十多分钟,这让大拉弱小的心灵受到巨大的伤害。
其实,不要说只有八九岁的大拉,即使是一个大人,在这种环境中面对这个冷漠诡异的男人,都会觉得害怕,何况大拉此次是来偷东西,心虚不已,以为这个似鬼非鬼的男人要惩罚他。大拉在房间内被控制住,这可急坏了在寨子东门望风的文廷。文廷一直徘徊在大门口,由于怕人看见,畏畏缩缩的,眼看时间过了很久,却不见里面的大拉出来。文廷迫不及待地在门口一边敲门,一边喊道:“大拉,在里面吗?你在里面吗?”
可是,在里面承受着巨大的恐惧的大拉并没有回应。
文廷惶恐不安,不过这个小鬼头,还是很够义气的,在这种异常情况下,他并没有私自逃离,而是顺着大拉的老路,爬上了大门口旁边的大树,然后跳到了围墙上。正在此时,从西门口走进来的善婶从远处看到文廷的举动,她心急火燎地大喊道:“喂,喂,你这小鬼,想干什么?”
狗急跳墙的文廷听到了善婶的喊话,从围墙跳到了树上,想赶快逃走,被匆匆忙忙赶过来的善婶呵斥住了:“小鬼,你老实告诉我,你想干什么?”
文廷吓得哑口无言,指了指屋子里面,许久才说道:“有人……在……里面!”
善婶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若无其事地说道:“里面当然有人了,怎么你对他那么感兴趣呀?我看你长得像村尾寨子的火狗,你应该就是他的儿子吧?”
文廷极不情愿地点了点头,然后默不做声。这时,善婶拿出钥匙,从门缝中伸进手去把锁头打开了,接着优哉游哉地走了进去,文廷也跟着溜了进去。善婶莫名其妙地看着文廷,说道:“你怎么这么晚了还不回家呀?你爸妈会找你的,好孩子,快点回家吧!”
文廷支支吾吾地说道:“我在等我同学,他爬进去了,都那么久了,还没有……出来呀!”
善婶听完,脸色大变,立即丢掉手中的农活工具,捶胸顿足道:“什么?惨了,惨了,这还了得,这孩子,怎么不懂事啊!”一边说,一边朝屋子里面跑!
毫无疑问,善婶心中有数,她朝家中划为小卖部的那个房间奔去!货物散落一地,她跨过货物,径直掀开门帘。只见两个人,一大一小,相对而坐。大人笔直地坐在凳子上,小孩面容惊恐地坐在床沿上。大拉仍旧抽泣着,只是没有了眼泪,坐在凳子上的男人似笑非笑,直愣愣地看着大拉。
对这个男人的异常举动,善婶并没有感到惊讶,因为这个人,就是她的丈夫!
善婶走到了丈夫善叔的旁边,俯首低语一番。善叔像听到了指令一样,缓缓地回过头来,指着对面的大拉,言简意赅地说:“他偷东西!”
善婶立即打断了善叔的话,温柔地说:“哎哟,你懂什么,这小孩,那么乖,怎么会偷东西呢?你真是的,快出去,快去隔壁房间。”善叔竟然乖乖地从凳子上站了起来,然后朝门口大步地迈了出去,看他走路飘飘然的样子,确实让人害怕,站在门口的文廷立即躲开让善叔走过去。善叔走了出去,善婶抱住床边的大拉,抚摸着他的头,柔声说道:“哎哟,孩子,你没事吧?不用怕,不用怕!”听善婶这么一说,大拉突然扑倒在她的怀里,大声地哭了出来,此时文廷也走了过来,看到了大拉苍白的脸蛋。
等大拉缓过来后,大拉和文廷先后把事情经过说了,其实,善婶早对此心中有数,她轻轻地抚摸着大拉的脑袋,说道:“孩子,想吃东西,也不用这样呀,小时偷针,大时偷金,偷盗行为是不对的。”她从地上捡了几包小吃,塞给他们,继续说道,“快回去吧,天色不早了,免得你们父母担心,我送你们两个回新一寨吧!”
大拉拭干眼泪,跟文廷一起走出门口。此时,天快黑了。善婶带着这两个小鬼从寨子出来,经过学校时,看到了大拉的母亲根婶。根婶刚想对大拉大骂,看到站在后面的善婶,就忍住了。善婶走到根婶旁边,耳语起来。
当时善婶跟根婶具体说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是根据善婶这一家人的特殊情况,估计善婶会说,这两个小孩被她的丈夫惊吓到,具体的偷盗事件就不要追究了,希望根婶开导一下小孩,不让这次惊吓对他们的心理产生阴影,不要再责怪小孩,等等。
果然,交谈过后的根婶脸色沉重,她遏制住满腔怒火,对根婶说了几句感谢的话,趁着夜色,带着两个小孩子朝村中的寨子走去。在路上,根婶对两个孩子唠唠叨叨:“你们呀,差点闯大祸,你知道善叔是怎么样的人吗?他是不正常的人呀!幸好这次善婶及时赶到,不然,你被善叔掐死都无处申冤,知道吗?善叔这几年来一直不正常,善婶就是怕他出事,所以很少让他外出,你看看,我们几时能见到他?平时乘着善婶在的时候,去买点零食就算了,你们竟然还去人家家里偷盗,真是不想活了。”
两个小孩听了,一路上沉默寡言,这是一次深刻的教训。这次惊吓事件对大拉多多少少有影响,此后他似乎乖巧了很多,极少光顾善婶家的小卖部。当时根婶对两个小孩说的语重心长的话语并非耸人听闻,善叔确实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变得行为诡异。众所周知,在他家中,他已经退居幕后,善婶成了一家之主。主要表现是,在农忙季节,善婶亲自到田间犁田或者耙田。要知道,在我村,这种粗活绝对是男人做的,但是,善婶并非离异,也非丧偶,却做本该由男人做的事情,而身材高大的善叔却一直待在家里,这实在让村民搞不懂。据说善叔怕光,怕讲话,用今天的话讲,他有自闭症,可是,作为他老婆的善婶不这样认为。
根据善婶对自己丈夫的回忆和观察,善叔的行为变得诡异是从5年前开始的。在此之前,丈夫一直安然无恙,这说明,从风水的角度来说,善婶家的这个房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善婶一家10年前就搬迁到这边,家人一直平平安安,六畜兴旺。
自从5年前寨子新开了一道门,一切就变了。开门事件应是根源,因为在此之后,陆陆续续出现了一些怪异的事情。
据说,最初,善婶的房子只有一个东门出去,面向村头方向,可是,要去村尾就稍微麻烦了,要从东门出去,然后绕到学校前面过,如果挑比较重的东西,无疑要做很多无用功,于是当时正常的善叔他别出心裁,准备在寨子的西边开个后门,即西门。当然,对于这么重要的事情,善叔极为重视,他请了技术尚可的地理先生。地理先生在西门附近用罗盘测来测去,认准了方向,然后看了个好日子。善叔请来泥瓦匠,开了一扇后门。
西门弄好了,它确实给善叔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挑尿桶浇菜呀,挑谷子去村中加工厂碾米呀,都方便多了。只是,殊不知,西门的开通在提供方便的同时,无形中也为死人提供了方便。西门落成3天后的晚上,善叔的弟媳等人带着两岁多的小孩来串门,大人谈天说地,不知不觉到了晚上9点多钟。突然,在门槛前玩的小孩子打了一个寒战,直愣愣地站在那里。善叔的弟媳上前一摸,发现小孩裤子下面湿漉漉的,并且伴随着一股骚味,原来是小孩遗尿了,这时小孩哭闹起来,料想小孩吃错了东西,拉肚子。弟媳立即抱着小孩来到靠近西门的茅厕。果然是吃错东西了,刚脱下裤子,小孩就哗啦啦地拉屎呢。
善叔的弟媳帮小孩擦屁股的时候,突然感觉到门口有一个孱弱的身影晃过,可是,许久却没有人从西门进来,她迟疑片刻,匆忙擦完小孩的屁股,走出去看。此时,小孩停止了哭闹,神情严肃地看着西门外面。
这不是一个两岁多的小孩应有的神情,莫非有人?善叔的弟媳抱起小孩,战战兢兢地走到西门口。大门外仍然有从院子内照来的微弱灯光,可是善叔的弟媳根本没有见到有任何人,于是抱着小孩回来,回到走廊时,心有余悸的她仍回头看了一眼,发现挂在茅厕门口的电灯晃动了一下,地面上的一个影子朝着自己这边被拉长,就如一个人跳了过来。她吓得浑身发抖,惊慌失措地抱着小孩进了房间。
当天晚上,在这样的充满喜庆氛围的场合,她没有向善叔夫妇说明这一情况。回到屋子里的小孩再也无法安静地玩下去了,始终哭闹不安,不管别人如何哄逗,总是显得心不在焉。尽管时间还早,无奈的弟媳一家只得先行回去。让善叔的弟媳感到后怕的是,当他们从西门出来后,离西门十几米远时,小孩竟然不再哭闹,并且有意识地紧紧地抱住母亲。还好,小孩回到家后,一直平安无事。因为此事毕竟模棱两可,所以多数人充当马后炮的角色。
其实,按照农村人的说法,小孩子是最能感受到诡异的东西的,比如,粤东地区的人在大城里买房子,会先请地理先生看房子的风水,甚至还有人带着小孩去看房,如果孩子在陌生的房子里安静、乖巧、愉悦,说明这个屋子是真正的吉屋,如果孩子一反常态,则此房子必有乾坤!由此看来,善叔的房子自从开了西门之后出现异常之事并非无稽之谈。
3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夜阑人静。在房间里睡觉的善叔听到围墙内笼子里的鸭子骚动,于是独自一人起床,拉亮走廊的电灯泡,走到笼子边,他并没有发现异常。此时正值深秋,夜晚有点凉,这座房子所处的地势比较高,但当晚却没有风吹来。
在走廊的灯光照耀下,善叔发现西门处有一个高大的影子映在门框上,被拉得很长,影子似乎会移动。善叔觉得非常奇怪,如果是鬼的话,怎么会有影子?不是说鬼没有影子吗,并且鬼走路时是没有声响的。正在这时,大门外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这脚步声让人觉得行走者步履蹒跚。当时还是正常人的善叔第一感觉就是对方应该是偷鸭贼,于是他蹑手蹑脚地走到西门边,然后打开了门……见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善叔具体看到了什么,永远没有人知道了,因为就从这天晚上开始,善叔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直到今天都没有完全好起来。当时在房间里的善婶也听到了外面的动静,在善叔出去之后,也就跟着走了出去。当她轻轻地走出走廊时,远远看到那个大门已经被打开,却不见善叔的身影。走到门边时,善嫂见善叔跪倒在门外的右边,正三叩九拜。善婶不知所以然,立即打了个寒战,她尖叫道:“阿善,你搞什么?”
跪在地上的善叔却把善婶的话当做耳旁风。善婶惊恐地走到善叔的面前,在微弱的灯光下,看到丈夫那张痛苦、惊恐的脸。善婶在情急之中破口大骂:“狗血泼你,狗血泼你!”善嫂看到善叔一副焦急却说不出话来的样子,善叔一直晃动着脑袋,脑袋老晃向西门右边正对着他的高处。
此处有一棵古老的黄梨树,大树的旁边已经逐渐成为善叔家放置生活垃圾的地方,一直以来,善叔一家都没有发现此处有墓地。可是,此时并不是善婶寻找真相的时刻,她想扶起善叔,却觉得他有千斤重,善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扶起,艰难地朝屋内走去。
突然,走廊的灯泡暗淡下来,灯丝却没有烧掉,给人的感觉是电压不足。奇怪,四下里无风,灯泡却随着上面的吊绳前后摇摆,善婶感觉到自己这边的灯泡影子时长时短。情急之中的善婶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恐慌了,拖着四肢无力的善叔朝家中走。
走到茅厕门口时,善叔突然挣脱了。似乎有一种巨大的力量附在善叔身上,他脸色凝重地跑到门外,奔向垃圾场。还没有等善婶反应过来,善叔在一团漆黑之中跪在地上,竟然用双手去刨垃圾堆。善婶一边追一边喊:“阿善,你要干什么啊?那是臭垃圾呀!”这声音在这个空旷的寨子中响起,听众却寥寥无几。
可是,失去理智的善叔对老婆的呐喊声置若罔闻,他仍然我行我素,竟然徒手翻刨着垃圾堆,真让人不可思议!
至此,很多人可能会想,垃圾下面肯定有不为人知的真相,这是肯定的,只是年代久远,难以理清。但是当天晚上的善叔并没有用双手验证真相。当善婶走到善叔身边时,他的手已经污秽不堪。善婶把善叔拖曳进屋,然后把西边的大门关得死死的。
善叔被拖回家后,走廊上的电灯恢复正常。善叔似乎有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竟然笑吟吟地望着善婶,一句话也没有说。细心的善婶发现善叔的右脸蛋上有一块黑色掌印,就像是画上去的,更诡异的是,掌印只有四根手指头。善婶立即产生一种不祥的感觉,她当时还以为是善叔刚才刨东西,然后用手摸了自己的脸造成的。可是,她用毛巾慢慢地擦拭善叔脸上的黑印,却根本无法擦掉!难道是善叔打自己造成的?但善叔的手掌并非有残疾,为何只有四根手指头?难道有鬼?面对丈夫脸上的异常情况,作为女人,善婶连个壮胆的对象都没有,又怕吵醒小孩,她立即关上房门,然后指着善叔脸上的黑印,轻声问道:“疼吗?”
善叔没有回答,突然朝门的方向傻傻地笑。善婶慌张起来,急得要哭,说道:“阿善,别这样好不好,我求你了。”但善叔并没有满足老婆的愿望,仍然像个呆子似的面无表情。善婶喃喃自语道:“麻烦了,应该是遇到不干净的东西了。”当天晚上,善婶心怀侥幸,以为丈夫只要好好休息一个晚上,明天就可以恢复正常。在她的诱导下,善叔终于上床睡觉了,可是他当晚显得非常烦躁,在床上辗转反侧。在旁边看护善叔的善婶一夜未眠,忧心忡忡。
第二天,天快亮时才合上眼的善婶发现善叔早已起床。她立即爬了起来,刚想出去找善叔,却见善叔站在窗户前,纹丝不动,全神贯注地看着外面。
善婶全然忘记了昨晚发生的事情,慢悠悠地问道:“阿善,你今天怎么这么早起床?”
善叔缓缓地转身,却没有说话。善婶惊呆了,因为这时的善叔跟昨天晚上很相像,她猛地想起昨天晚上的事情,却发现善叔右脸上的黑印已经退去。善婶疾步走到善叔身边,摸了摸他的额头道:“阿善,你没有什么事吧?”
善叔笑了,嘴角边挂着复杂的笑意,不紧不慢地说道:“我……没事!”
善叔的语调与往日全然不同,变得冷漠、简单。善婶急了,立即去老寨子找几个叔伯。众人到来之后,平素热情的善叔却对他们冷眼旁观,仍然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娱自乐,还时不时莫名其妙地发笑。综合昨天晚上善叔的表现和之前的蛛丝马迹,众人展开了讨论。大部分人认为善叔中了邪。但是邪从何来?众人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善婶屋子这个地方是个难得的好地方,可以说方圆一千米连座墓地都没有。这个寨子是村中最吉利的寨子,哪里谈得上有鬼?再者,即使有鬼上身,也是冤有头债有主,怎么惹了个无名鬼呢?
无论如何,人命关天,驱鬼要紧。第三天,善叔原来的老邻居曾开来了,在善叔的家中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祭祀活动,善婶家人跪拜了大半天,搞得筋疲力尽,却没有如愿以偿,因为连曾开都不认识这个无头鬼魂,又谈何驱鬼呢?当然,也可以说,曾开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不是万能的。祭祀后,善叔稍微好点,除了爱笑和行动缓慢,能与老婆和小孩正常沟通。从此之后,善婶不再让他干重活。久而久之,他丧失了劳动能力!因为平时外出他会迷路,又或者会让陌生小孩受到惊吓,善婶就劝他少出去。善叔几乎总待在自己的寨子中,导致很多其他寨的小孩根本不知道他。
就这样,一个原本重要的劳动力在善婶家中消失了,善婶却成为了一家之长,在各种要家长出面的活动中,都是善婶抛头露面。这次大拉和文廷偷东西事件只是一个插曲而已,他们家发生的零零碎碎的事件还有很多,因为并不影响故事的结局,所以这里暂且不提。
如果善叔就这样永远“笑”下去,那么对他来说,实在是太不公平了!还好,让人欣慰的是,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个夏季,村头的老寨子沸腾了。因为寨子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要回来了,他是我村唯一的台湾同胞。20世纪90年代,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已经开始变得友好,很多失散多年的亲人通过各种途径彼此联系上了。
令老寨的士叔觉得奇怪的是,官方联系到他,说他还有一个堂叔生活在台湾。后来士叔问了一位老人,确认了这个消息。果然,经过反复确认,那人就是自己的堂叔。过了半年,这位让全村人瞩目的老人回来了。根据辈分,我应该称他为叔公太。当时,他已经八十多岁,头发掉光,步履蹒跚,但身材高大,村中跟他最亲的就是他的堂侄士叔了。
村中认识他的人已经寥寥无几,只有几个年纪大的人对他还有点印象,但这几位老人也是耳聋眼花,很难沟通往事。估计这位叔公太的生活还可以,他保养得很好,讲话虽然不利索,但思维还是很活跃。他讲述了惊人的过去:他是在解放战争后期加入国民党的。当时他赌博欠债,走投无路,稀里糊涂加入国民党。后来,他在台湾娶了老婆,生了孩子。
加入国民党之前,他的母亲早在他年幼时饿死,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被卖给外地人做童养媳,失去了联系。而唯一的亲人父亲死时,他只有十几岁,当时他有钱买棺材,却遇到了农村所说的“六十年‘大土王’”!
在客家民俗中,人死之后,用棺材埋掉,一般在3年后的八月初一进行捡骨头的活动,然后再葬死者。但是,这位叔公太的父亲偏偏遇到了“六十年‘大土王’”,这表示,他的父亲只有在60年之后才可以捡骨头,一般遇上这个,死者也就很难再享受捡骨头的待遇了。60年多么漫长啊。不要说儿子,有些命不好的,连孙子都死了啊,谈何“捡骨头”!但是,没有想到的是,60年之后,这位叔公太并没有死,只是他还在台湾。60年,一个甲子,一个轮回。地下的人并没有享受应得的待遇,于是开始兴风作浪。
叔公太安顿下来几天之后,要侄子带路去看望父亲的坟墓。凭借六十多年前的记忆,勉强来到我村学校周围,却再也找不到埋葬父亲的地方了。要知道,当年这里根本没有小学,小孩还是念私塾呢。
一些老者冥思苦想一番,在他们的记忆中,学校附近根本没有挖到墓地呀。
后来,叔公太说,他父亲的墓地旁有一排野生的黄梨树。士叔一找,发现那地方竟然在善婶的房子附近,即西门的对面不远处。村民震惊了,看来善叔的诡异变化并非没有原因啊。
由于长年累月受到上边泥土的侵袭,老梨树下的棺材被掩盖得很深,挖出来之后,棺材的大体轮廓还在,但腐烂成泥土了,里面的骨头,据说仍然存在。
叔公太的父亲被重葬那天,声势浩大,毕竟叔公太有钱嘛。当时他几乎请了我村全部60岁以上的老人参加祭祀活动,并且给每人发50元。估计这次声势浩大的祭祀终于让他地下的父亲安息了。让人觉得无法明白的是,之后善叔一家并没有搬走,而善叔却一天天地好起来,现在几乎跟常人一样!
挽救善叔的叔公太在当年返回台湾后不久逝世。善叔至今仍对这位叔公太满怀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