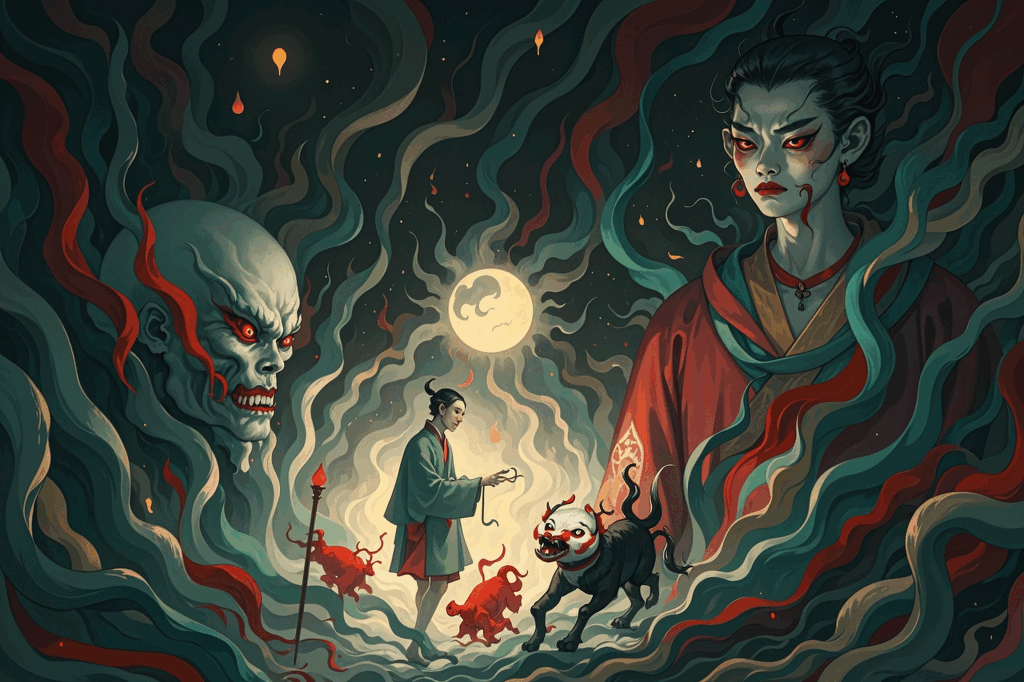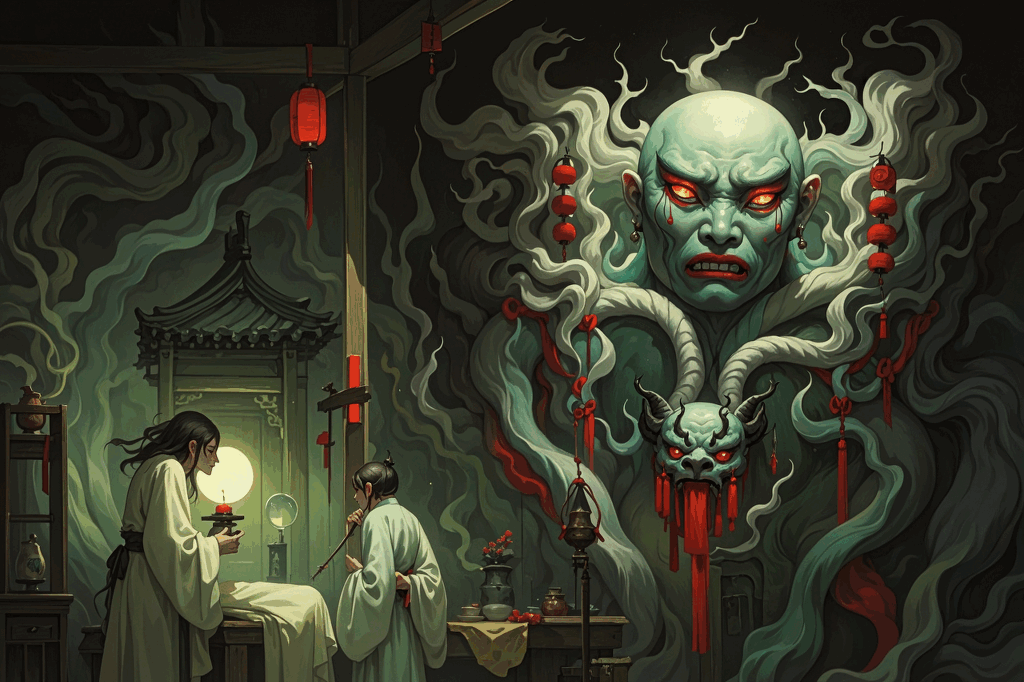去年正月,当我偶尔回到自己土生土长的农村老家,见到原本只过知天命年纪的毛哥,不禁感慨万千。他的年纪与相貌大相径庭,那张面孔显得极为苍老,而原本焦黄浓密的头发如今寥寥无几,两鬓略显鬓白。有人说时间是治疗创伤的良药,但对于他,时间却似乎显得多余,曾经的痛苦让他一直以来苟延残喘地生活,而后来因为妻子的病死、女儿的出嫁,更让他如行尸走肉般生活在人世间。
有人说,天下幸福的人都一个样—家庭和睦呀,财富充裕呀,身体健硕等,总之,这些人总会露出一张让不幸的人生气的面孔,在世人的面前显示他们光鲜的一面。不幸的人却不尽相同,但不幸的事发生在我村,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点,那绝对离不开神鬼传说,不然就不叫闹鬼村了!
首先报告一下岁数与职业:那一年,我8岁,小学二年级;毛哥28岁,村干部之一;来叔36岁,四个女儿的农民父亲。有一天,中午放学后,学生们回各个寨子的家中吃午饭。当我们小学生经过村中的新三寨(寨子名称)时,看到了七八个陌生的青壮年,他们围在新三寨的门口,个个神气十足,指指点点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件,好奇的学生和路过的村民都驻足观望。
当时的新三寨只住着一户人家,寨子的类型是单家园屋,业主叫来叔。来叔本来跟毛哥同一寨子,后来他自己建了新三寨,一家人搬了进去。看来在那个中午,来叔并不在家中,不然屋门外如此喧闹,里面应该不会毫无动静,据后来村民证实,当时来叔一家确实不在其中,大门用一把大锁锁住,而大门旁边的鸡栅早已鸡去栅空。门口的这些人,似乎并不认为来叔早已离开村子,他们坚信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两个大人拖儿带女能去哪里呢?
从这些人的阵势看来,像跟来叔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一阵叫嚷之后,其中一个人从屋檐外搬来两把梯子,两人扶住,他灵敏地攀上了梯子,下面的人递给他两根竹篙,他立即握着竹篙在屋顶上乱捅,顿时,整个屋顶被弄得一片狼藉。下面的几人也拿起几根较长的竹篙,直接捅屋檐,瓦片立即纷纷坠落,地面上瞬间也是狼藉一片。看热闹的人个个神情肃穆,突然,一个小孩尖叫了起来:“拆屋呀?”
大门外面站着一个略显发福的中年男人,衣着光鲜,皮鞋铮亮,他回过头来,望了望那个说话的小孩,露出了一丝邪恶的微笑,然后向众人点了点头,说道:“是拆屋,被逼的!”
此人话刚说完,更粗鲁、更过火的动作出现了:下面的人递给梯子上的人两根粗绳,梯子上的人把粗绳套在几个屋顶的几根横梁上,再绕几个圈,紧紧拴住,然后立即下来。接着,七八个人用力拉绳子的两端,大喊“一、二、三”,只听到“砰”的一声巨响,横梁连着屋顶被拖了下来,瞬间地面上尘土飞扬,一座光秃秃的泥砖房子裸露在众人的眼前。
中年男人捂着嘴鼻向后退了退,回过头来,用教训子民的口气对众人说道:“没什么好看的,大家都回去吧,这就是逃避计划生育政策不去结扎的人的下场。小朋友快去告诉你们的父母。”小孩子个个垂头丧气,耷拉着脑袋离开。
正在此时,毛哥慌慌张张地跑到屋子前,见到眼前的情形脸色大变,捶胸顿足地大声叫道:“主任,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最后日期是后天早上,到时不见人再由你们自行决定,怎么现在就动手了,并且也不先告诉我?”
中年男人气定神闲地望了望毛哥,严肃地说道:“已经到期限了,如果不这样做,怎么会有威慑性?其他符合条件的待结扎妇女怎么会乖乖前来?现在我们不要跟他们谈条件,本次符合条件的待结扎妇女必须无条件地进行结扎,否则把他们家的屋顶全部掀掉,让他们无家可归!不然,计划生育任务难以完成。”
毛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显得很无奈:“主任,我不是跟你说过嘛,我已经知道了曾来的去向,只要我找到他后,好好跟他谈,应该没有大问题的,现在你把他家屋顶都拆了,我怎么还好意思再跟他谈?”
中年男人语气强硬地说道:“阿毛,这是你的事!我的事就是把不配合工作的人的屋顶全部掀掉。”
毛哥听完,摇了摇头,一言不发地走了。毛哥深知自己的工作难做,为了配合镇计生办驻村的工作人员工作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他必须两边讨好,这边和颜悦色地面对镇政府派来的人员,那边又要到村中各育龄妇女家中做思想工作,宣传国家政策。毛哥确实是个好干部,但是,平心而论,他的这种工作展开确实非常艰难,因为有时代的特殊性。
我曾经作过一次粗略的统计,在我村,出生在1970年至1980年间的人,兄弟姐妹人数在4个左右;出生在1980年至1990年间的,兄弟姐妹人数在3个左右;出生在1990年至2010年间的,兄弟姐妹人数普遍为2个。故事开头的一幕发生在我读二年级时,当时是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村民生3个小孩左右,突然间,不问青红皂白强迫最多只能生两个小孩,那一代人怎么能在短时间内接受这种观念呢?特别是那些频频生女儿的夫妻,他们怎么会主动走入结扎的队伍呢?因此,当时的毛哥做了一份很难的工作,因为工作,他成为一部分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本来都是本村本寨的,却因为这种事情反目成仇。后来,毛哥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故,有人说是毛哥那时的工作导致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有点牵强附会,毕竟那是工作,毛哥并没有损人利己。
为逃避结扎,在工作组下来的时候,有人上山逃避,跟工作组玩捉迷藏。后来没有办法,政府的要求更加严格,有些人只能出外逃避了,比如,来叔家就是如此。据说,掀瓦时,一家人早已逃到他乡自谋生路。
据说,当时毛哥成为村委的一员时,老母亲赵伯母极力反对,因为她在村里生活了三十多年,她深知我村村民的秉性。但是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也找了赵伯母,做了赵伯母的思想工作,赵伯母才勉强同意。几年之后,计划生育工作如火如荼地在村中进行,而她的儿子也必须参与其中,为此,赵伯母跟毛哥起了口角之争。
一个傍晚,赵伯母警告毛哥说道:“阿毛,你就不要回村委做事了,我担心你!”
毛哥看着老母亲,问道:“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显然毛哥是明知故问,其实他也清楚:与人树敌,祸患无穷!老母亲苦口婆心地说道:“只让人家生两个子女,就拉人家去结扎,这会犯众怒的!这合理吗?如果你老婆以后才生两个小孩,就去结扎,也不可能吧?”赵伯母说完,妻子也来劝说,妻子说完,连兄弟也来劝说,可谓轮番上阵,让他应接不暇。可是,毛哥却有他自己的道理,他对着众人说道:“你知道现在中国有多少人吗?如果大家还是这样毫无节制地生,以后一个地球怎么可以住下那么多人?”
显然,毛哥对着一大堆农村人谈论地球的话题,有点对牛弹琴。果然,还没有说完,赵伯母立即骂道:“你放狗屁,这世界,多一个人不多,少一个人不少,别人生几个,你又不是他们的爹娘,不用你养活,关你什么事?”
毛哥见到母亲大发雷霆,也不敢反驳,过了一会儿,他轻声细语地对赵伯母说:“妈,我又没有拉别人去结扎,只是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而已,这有什么?你不要把事情想象得这么严重。”
听到毛哥还不把这当回事,这下赵伯母可急坏了,她连忙说道:“哎呀,阿毛,你不知道,村里人怎么说你的呀,流言飞语可多了。说你这样做,是让别人断子绝孙呀,以后会遭报应的,你自己也会不得好死啊。”
赵伯母说完,一脸悲伤,现场陷入了死寂,这确实是可怕的骂人言语呀。毛哥当天晚上在床上辗转反侧,想了很多,他几乎因为母亲的警示而动摇了自己的立场,他准备不干了。当他第二天去书记家说明原因时,却遭到了书记的当头一棒,书记娓娓道来:“阿毛,你也真是的,怎么跟落后群众一般见识,党就需要有先见之明的人才,如果现在做这些事情都畏畏缩缩,以后如何去做大事?”
毛哥留了下来。当然也有人私下传言,书记一直在培养毛哥做接班人。或许就是这个诱惑让毛哥对赵伯母的话置若罔闻。
从此,发生在毛哥身上的诡异事一桩接着一桩。
某晚子夜时,寨子里寂静无声,毛哥和身怀六甲的妻子躺在床上。当时的毛哥还没完全入睡,突然,他听到邻居上堂的房子有开房门的声音,这让毛哥觉得诧异,自从来叔搬去新三寨之后,这座房子就一直空着,难道在外面逃避计划生育的来叔回来了?毛哥立即起床,穿好衣服,准备去看个究竟。
毛哥的举动惊动了一旁的毛嫂,她眯着眼睛轻声问毛哥:“阿毛,这……深更半夜的,你……出去干什么?有什么事不可以等到明天吗?”
毛哥嘘声道:“我听到声响,不知道是不是来叔回来了。他可是计划生育指标中的人物呀,我要去跟他好好谈谈。”毛嫂并不在意,倒头而睡。
毛哥拿了一把手电筒,为了探到实情,他并没有打开手电筒。屋子外面很暗,毛哥蹑手蹑脚地走到了上堂,果然,一向上锁的来叔房子的房门竟然半掩着,毛哥断定,来叔肯定是偷偷回来办什么事。他悄悄地凑近门缝向里望去,可惜里面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过了一会儿,毛哥的眼睛适应了,只看到了几张陈旧的桌凳和一些废弃的农用工具,这都是来叔当初搬去新三寨时留下的。
就在毛哥屏气张望的时候,木棚上传来一阵轻轻的脚步声,或许是来叔回来怕人发现,动作变得小心翼翼。毛哥定了定神,然后朝着门缝里喊道:“来叔,来叔,是不是你回来了?”
棚上的脚步声戛然停止,而睁大眼睛的毛哥,见到从棚上飘下一个白影。这身影非常瘦小,缓缓停在屋内的角落,这人徐徐地转过身来,惊愕地看着毛哥。
毛哥定睛一看,哎哟,这不是小芳吗?毛哥惊喜交加,显然毛哥认为,来叔的女儿小芳回来了,来叔肯定也是一起回来的。毛哥立即把其中的一扇门推开,闪进了房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就在毛哥进来的一刹那,那扇门竟轻轻地合上了,同时,一阵发霉的味道涌进毛哥的鼻尖。毛哥立即回头看着关闭的房门,觉得怪异,他不确定自己进来时有没有顺手关门,此刻的他并没有丝毫害怕,他立即打开了手电筒,朝房间的角落照去。人呢?人呢?明明小芳刚才还在角落里,此刻却踪影全无。
难道是自己眼花了?毛哥额头上开始冒汗,但此时的他仍确信来叔在棚上,他把手电筒照向棚上的入口,然后轻轻地叫道:“来叔,来叔,你是不是在棚上呀?”他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内异常沉闷,一粒粒微尘在手电筒光束中舞动,房间内也充斥着灰尘的味道。可是,毛哥喊完,棚上仍然悄无声息。突然间,房间的角落传来了小女孩微弱的声音:“毛叔,我……爸爸……不要我了……”
毛哥立即把手电筒照向角落,果然见小芳蜷缩着身体,扑在一张矮凳上。毛哥走上前,发现小芳的双眼瞳孔很大,白多黑少,表情深沉,好像非常不高兴。
毛哥满肚子的疑惑,问道:“小芳,你爸爸呢?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来叔是不是也回来了呀?”
此时的小芳却一言不发,好像受了很大的委屈。毛哥不知所措,两人就这样对峙了一阵,突然小芳紧紧地抱住毛哥的双腿,放声痛哭:“毛哥呀,我爸爸重男轻女,不让我去上学呀,我都9岁了还不让我去上学,我要去上学,我要去上学呀……”在黑夜里,这哭声真是让人揪心呀。事后证实,离得不远的邻居也在这晚听到了这间房里发出的声响,但并不是小孩的哭声,而是哎哎哟哟的和尚念经声。
当时的毛哥听了小芳的哭诉,也是悲从中来,他轻轻抚摸着小芳那幼稚的脸庞,竟然摸到了冰凉的眼泪。他叹了口气,安慰小芳:“小芳,你别哭了,错不在你,都是你爸妈的问题,生那么多小孩,一家有那么多人要吃饭,也真不容易呀。你爸爸呢?我跟你爸爸说说,叫他无论如何,也要让你去上学。”
小芳擦了擦湿漉漉的眼眶,渐渐地停住了哭闹,声音仍然哽咽着,许久,她用冷冰冰的语气对毛哥说:“毛哥,都怨你,是你们逼走了我爸妈呀,如果我们还在村子里生活,我爸妈会让我去上学的。”
毛哥无言以对,他疑惑片刻,说道:“小芳,政策的事情,你小孩子不懂,再说,我也没有逼走你爸妈呀。对了,你爸爸是不是也一起回来了?我这就去跟他说,别去他乡东躲西藏了,搬回村里来,这样你就可以去上学了。”
小芳摇了摇头,眼里露出了一丝哀怨,说道:“不,不可能了,我爸妈是不会跟我回来的,他们一定要生个弟弟。”
毛哥觉得怪异,就在小芳摇头的瞬间,他看到了小芳惨白的脸蛋。小芳指了指木棚的入口,接着说道:“毛哥,我是跟我奶奶回来的。”
奶奶?思绪混乱的毛哥艰难地回忆着小芳的奶奶是谁?不是马伯婆吗?可马伯婆早就死了!我的妈呀,死去的马伯婆怎么会带她的孙女回来呀?毛哥心里发凉,撒腿就跑,跑到门口时,原本只是掩上的门却在手忙脚乱中无法打开,后边似乎传来小芳那愤怒的声音:“毛哥,是你逼得我没书读呀!”毛哥疯狂地扳开了门,慌不择路的他,刚跑到门口,额头竟然重重地碰到了走廊上的墙壁,他立即觉得眼前一黑,晕在走廊上。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晚上去挑担子回来的邻居阿田哥经过走廊时被倒在地上的毛哥吓了一大跳,立即喊来了毛嫂和邻居,他们把他抬进了家。毛哥一醒来,就急切地问道:“是不是来叔回来了?”邻居面面相觑,先后离开。或许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即使知道的人也不会说出来,谁不知道毛哥找来叔的目的?毛哥在第二天彻底清醒的时候,不确定昨晚的一切是真实发生过的还是只是一个梦境。后来,在大白天,毛哥又亲自到来叔的屋子检查,发现墙角有一块肮脏的抹布,料想是以前小芳穿的衣服。
后来村里有人传言,那天晚上,来叔确实没有回来,而是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偷偷回来,并告诉了他亲戚一个惊人的噩耗—他年仅9岁的女儿小芳在他乡因为迟几年让她读书而赌气,跑到公路时,给摩托车撞死了。悲哀呀,记得这个小芳跟我同年,如果她没有跟着父母背井离乡的话,现在估计为人妻为人母了。
几个月后,毛哥的第一个小孩出生,带把的,俗名叫“保古”,保佑的“保”,或许在毛哥的心目中,这个名字有特殊的含义。
保古出生后,毛哥一家其乐融融。虽然我跟毛哥不同寨,但保古那小孩,我对他还是有点印象的,因为他的头发跟毛哥的头发大相径庭。毛哥兄弟姐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头发古怪,咱中国人的头发都是黑的,但毛哥的头发全都是黄的,并且有点卷。当时,很多村民在私下里说,毛哥的头发那是从毛哥的父亲身上遗传的,而其父亲为何如此?是因为他的奶奶被……反正我没有见过毛哥的父亲,所以此论不足采信。可喜的是,保古头发却发生了变异(也可以说像他母亲),乌黑一大片,并且这小孩打小就聪明伶俐,讨左邻右舍喜爱。毛哥家平静地度过了3年,三年后,又有不寻常的事发生。
毛哥毛嫂晚上努力地“耕耘”,准备再要个孩子了。但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因为他的第二个小孩的出生意味着毛嫂也是政策内的节育妇女了,必须结扎!
据说,当毛哥的第二个小孩刚刚出世的时候,赵伯母迫不及待地跑到媳妇的产房(其实就是睡房),看了看小孩的裤裆,大失所望,因为是个小女孩,赵伯母当时连句“恭喜”的话都没说就外出做田埂去了。20世纪90年代,我村村民的观念已经开始慢慢转变—有一个儿子和女儿也算不错了。但赵伯母老是要跟她自己的那个年代对比,她可是生子5个儿子和3个女儿的光荣母亲呀,并且她也深知毛哥这个儿子的性格,生了二胎绝不会再要第三个小孩的。
果然,在生完第二个小孩不久,在一次借口去镇卫生院看病时,毛哥主动带他的老婆去结扎了。几天后回来,赵伯母知道真相后,那可叫翻了天,她勃然大怒,呼天抢地,据说当时毛哥家里唯一的电器—21英寸的黑白电视机—都被她摔坏了,搞得当时没有电视机而经常去毛哥家看电视的人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电视看呢。后来,人们才意识到,当时他们争吵的含义。现综合不同的流传版本整理如下:
赵伯母摔完电视,坐在长凳上,怒道:“毛古,你这个狗叼的,你老婆结扎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我商量?”
毛哥底气十足,反问赵伯母:“还要商量什么?我都是两个小孩的父亲了,又不是小孩子,这样的事情还商量什么?”
赵伯母不甘示弱,仍然摆出母亲的威严,说道:“但有人这样做吗?现在不生就不生,还有谁去结扎的?结扎就是断了命根,谁知道以后的事,如有三长两短,你会悔不当初的!”
毛哥不在意地笑了笑,安慰赵伯母说:“哎,妈,你这是杞人忧天,人人都不知道以后的事,做人不用活得那么累呀,现在都两个小孩了,最好不过的了。”
赵伯母摇了摇头,估计是觉得“朽木不可雕也”,长叹一声:“唉,反正我也老了,管不了那么多了,总之你老婆去结扎,你就是木令屎(愚蠢至极),以后的事情我也看不到,到时我早入黄土了,你好自为之吧!”
最终,两人不欢而散,当时的赵伯母已是高龄老人,再加上确实是有点庸人自扰,自寻烦恼,不久身体就垮了,一年后便告别了人世间的纷扰,长眠于黄土之下。这次的吵架成为毛哥后半生挥之不去的记忆。
来吧,要来的都来吧!
那一年,保古9岁,是这个可爱的小男孩在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生活的最后一个年头。
那天,毛哥要去寨子的后山砍竹,由于是周末,懂事的保古也要跟着爸爸上山帮忙。人都有走背字的时候,这时候,应注意调整自己的状态。比如,司机如果睡眠不足或者体虚,容易精神恍惚,这时应该好好休息,调整好状态再出车。但毛嫂并没有认识到这点,当出现不祥的征兆时,毛嫂并没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最致命的一点。
早上上山前,毛哥去另一间房准备上山的工具,保古坐在餐桌前吃早餐。突然,保古看到一个小孩子闪进了上堂来叔的屋子,保古愣愣地端着碗,目不转睛地盯着门口。
毛嫂看到保古呆呆的,走了过来,凑近保古的脸前,问道:“保古,你怎么了?”
保古漫不经心地说道:“妈,刚才进入上堂屋子的小孩子是谁呀?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出来呢?”
毛嫂莫名其妙地看着保古,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妙,因为上堂来叔的房子不可能有人,这个房子这几年都已经给邻居家做柴房,大清早的,怎么可能有小孩子跑进去呢?
疑窦丛生的毛嫂,突然走出了房间,脚步声很重地走向上堂,狠狠地把门踢开了。柴房里光线暗淡,到处是密密麻麻的蜘蛛网,毛婶清了清嗓子,向里面喊道:“有人吗?”见没有回应,毛嫂把门关了起来,然后回到房间,摸了摸保古的额头,自言自语道:“不烧呀,大清早,怎么时运那么背呀?”这时,毛哥过来催保古出发,毛嫂赶紧把刚才的情形告诉了毛哥,两人嘀咕一阵,当天取消上山作业,让保古待在家好好休息。
毛嫂做对了。几天后,毛哥上山,带上了保古。
事发后,毛哥回想时常感叹道:“真是百密终有一疏。”当时,保古跟着毛哥走,心不在焉似的,老是回头看,还时不时地自言自语,但毛哥当时并不在意,料想小孩子就是这样调皮的。毛哥万万没有想到,无形中有东西跟着保古。
毛哥家的山在后山三四千米处,到了后山,毛哥手脚麻利地忙碌了一阵,很快竹子就砍好了,在整个作业的过程中,毛哥跟儿子离得不远,毛哥不停地讲一些故事给儿子听,当要离开的时候,毛哥喊道:“保古,咱们回去了。”
但是,保古并没有回应爸爸的话,毛哥走到保古停留的那个大草坪,发现保古正聚精会神地望着头顶的那棵叫“高山望(一种野果)”的参天果树。突然,高山望的一根树枝异常剧烈地摇晃了起来,保古大喊了一句“小心”,只见树枝上一个黑色的东西飞走了。
毫无疑问,这只鸟是一只非常有灵性的鸟,但保古对一只鸟喊“小心”的话,实在太过离奇。毛哥有点疑惑,继续喊:“保古,别玩了,走啦。”
但保古仍然站在原地,仰着脖子,看着那棵树。就在毛哥想发火的时候,保古回过头来,嬉皮笑脸地指了指树枝,怯生生地对毛哥说:“爸,我想吃那个!”
原来那小子想吃野果,不过当时野果还没有完全成熟,有点涩,但如果摘回家,用纸袋封起来,放在箱头橱角,过几天就被催熟了。毛哥劝保古说:“那果子还不熟,过两星期我再来摘给你。”
可是,那小子不愿意,非要不可。原本听话的儿子因为几个果子撒娇,这让毛哥有点恼火,不过他还是忍住了,放下了手中的工具,一声不吭地朝那棵树走。而人生的变故就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发生!
高山望的树根长在十几米远的斜坡上,果树枝繁叶茂,树枝和叶子刚好覆盖了坡下的整个大草坪,要爬上树,必须从树根的那边爬。当毛哥走到树下的时候,发现树下竟然有几个大石头,他跳到了一个石头的上面,发现石头摇摇欲坠,于是他立即跳到了泥土的一边,然后特地把解放鞋脱掉,放在石头上,接着,攀树而上。吃山住山的毛哥,爬树还是保持着传统的敏捷,他很快就攀到了树顶,儿子正好就在他的脚下。毛哥手起刀落,几根树枝藕断丝连,挂在树干上,毛哥在树上大喊:“保古,保古,走开,树枝要掉下去了。”保古还算清醒,敏捷地跑到了大草坪的周围,接着,毛哥再一次对连着树皮的树枝砍了几刀,树枝“啪”的一声,落在了大草坪上,旁边的儿子立即活蹦乱跳地跑了过来,兴奋地摘着树枝上的果子。
毛哥把镰刀放进后背的刀卡里,然后小心翼翼地沿着大树向下爬,接近树下的时候,毛哥竟然跳了下去。毛哥实在是太健忘了,就在这一瞬间,恐怖的一幕发生了。
毛哥重重地跳到了一块石头上,本来就松动的石头立即发生了摇摆,在石头上的毛哥大叫一声“不好”,跳到了另外一块石头上,由于惯性太大,毛哥又跳到了旁边的土堆上才得以自保。几块石头立即轰隆隆地向下滚,刹那间整个山涧地动山摇。
刚在土堆上站稳,毛哥这才醒悟过来,儿子在下边啊,他的脸色立即变得惨白,撕心裂肺地叫喊:“保古,走开,走开,石头翻下去了!”他一边喊,一边疯狂地往下跑。
蹲在大草坪处的保古正在忙着摘地上树枝上的果子,当他听到爸爸的喊叫声和惊天动地的石头翻滚声,回过头来朝山坡上望了望,吓得目瞪口呆,动弹不得。的确,9岁的小孩一般很难及时应对这种突如其来的灾难。
一块石头狠狠地砸在了保古的身上,一个弱小的身躯在顷刻间倒下。毛哥亲眼看到了这人间惨剧!
那一刻,毛哥如遭雷击,瘫软在地,感觉天旋地转,他面目扭曲,却欲哭无泪。毛哥终于跑到了保古的身边,抱起血肉模糊的儿子,拼命地摇动,但儿子一点反应都没有。
毛哥抱着保古疯狂地往家走,一路上用嘶哑的嗓音叫喊:“救救他,救救他!”然而,回到家后,保古已经断气。据说,当时的石头砸到了保古的躯干,虽然脖子和腿脚完整无损,但内脏完全破碎,更加恐怖的是,肠子都流出来了,真是惨不忍睹。
保古的母亲更是哭得死去活来,不断地质问毛哥:“究竟为什么会这样!”但毛哥两眼无神,他真的说不出口,是自己亲手杀死了儿子!
从此,保古的母亲变了,逐渐向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的形象靠拢,可悲的是,当时她才三十来岁。
不久,来叔回来村里一趟,说他老婆终于生了个胖墩墩的儿子。有人掐指一算,来叔儿子的生日跟保古的忌日相差不过一个月,或许这是众人的穿凿附会。
再过了几年,毛哥的老婆由于儿子事件的打击,身体也就垮了,最后病逝。而在前几年,毛哥的年仅20岁的女儿外出打工,很快找了一个外省的男朋友,连酒席也没办,领个证就算是结婚,被带走了。由于路途遥远,很少回来。现在,只剩下孤零零的毛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