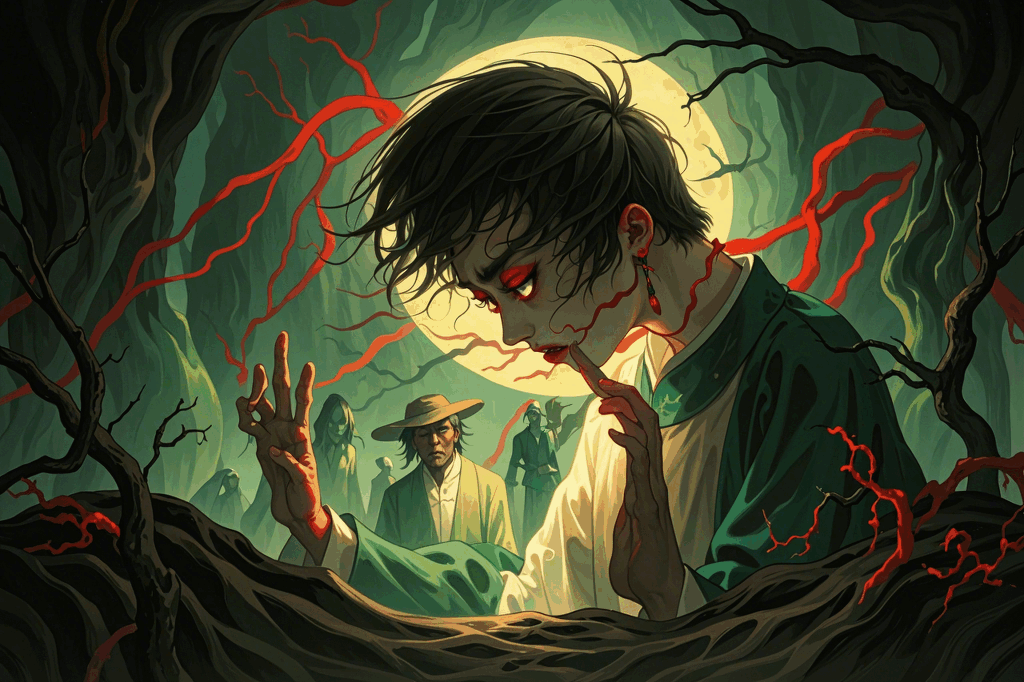18
阿娘替我扎好了额头上的白布条,送我出了门。
我走上那条走了无数遍的小路,身后跟着的,是村里的男女老少。心里想着的,却是过去这几个月,奶奶跟我讲过的话。
奶奶刚住进福耄窑的那几天,总是问我,阿爹阿娘怎的不来送饭,让我一个小娃娃跑来跑去,累得慌。
我将阿娘的话,原封不动地说给奶奶听。
“阿爹阿娘想多留您一段日子,我身子小,村里人不留意我,也就不查我。”
奶奶听后,便不再问了。
而我每天送饭时,也会跟奶奶讲讲,阿爹今儿个又做了什么事,说了哪些话。
又过了些日子,奶奶在我说起阿爹时,总会打断我的话,然后问我:
“狗妮儿,你今儿又做了什么事,见了哪些人啊?”
渐渐地,我和奶奶的窑中话,不再是阿爹、阿娘,和村庄。
奶奶给我讲她的一生。
从出生起,她就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是祖母,最后,是福耄。
“可我从来没有一刻,是我自己。”
那时我不明白奶奶的话,她怎么不是她自己呢?她一直都是她自己啊。
听着我的不解,奶奶的眼里,总是闪着泪光,拉过我的手,轻轻地拍着。
“是啊,狗妮儿说得对,一直都可以是自己。”
奶奶说,狗妮儿这个名字,家里人叫,尚且有几分亲昵,但是外人叫,不合适。
奶奶问我,想不想跟村里的男娃一样,有带着姓的名字。
我没多想便点了头,若是我的名字也带上了姓,那我就是村里第一个名字里带着姓的女娃了。
“就叫周思寻吧。”
“不管往后别人说什么,你都得想清楚,你想要做的是什么。”
“想清楚了,就奔着你想做的去追寻。”
“奶奶只希望,你的一生,可以是你自己。”